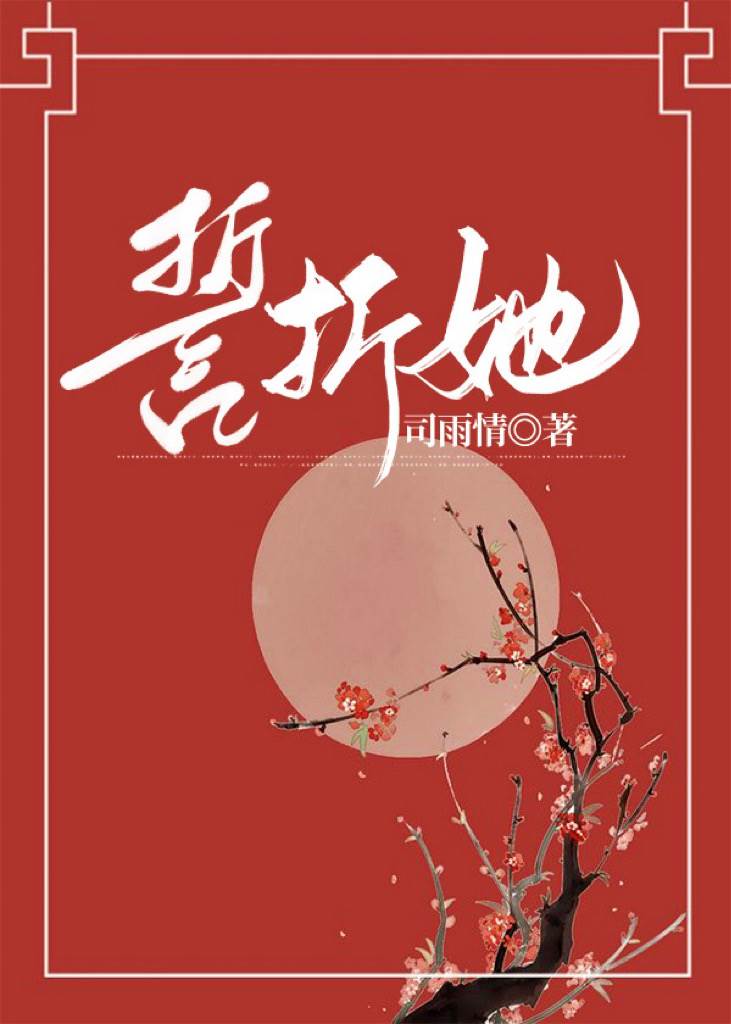《如意事》 六百六十八 捅破
“皇后,這又是何?”昭真帝向海氏問道。
海氏面雪白地搖頭:“臣妾不知……這不是臣妾的東西。”
說著,看向仍跪在那裡的掌事嬤嬤,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不那麼抖:“嬤嬤可知是何嗎?”
掌事嬤嬤連忙也搖了頭:“婢子也不曾見過,這本不是從玉坤宮中帶出來的!”
不知這裡頭究竟是什麼東西,但的的確確不曾見過,這是實話!
昭真帝的視線落在那隻被捧到面前的黑布匣上,道:“打開。”
見那緝事衛應聲解下了包裹著匣子的黑布,海氏十指攥發。
那是一隻四方黃木匣子,且上著鎖。
“皇后可知鑰匙在何?”昭真帝再問。
海氏聽得渾冰冷,幾乎是聲道:“陛下……此當真不是臣妾所有,臣妾也不知是何人放在此……或是,或是此前在此住過的人留下來的也說不定!”
此時此刻,繃著腦子裡隻一個聲音——絕不能認下此!
將的反應看在眼中,昭真帝再看向那隻匣子時,聲音微帶了些冷意,重複道:“打開——”
還未曾被打開,海氏便急著否認,仿佛已經“預料”到匣中之非同尋常——
至於如何不同尋常,還須親眼看過才知道。
隨著兩聲輕響,那把銅鎖便被林統領拿匕首輕易撬開了來。
林統領親自將黃木匣打開,待其之映眼簾時,不由出意外之。
“陛下……是蟲!”
昭真帝微微皺眉,示意他捧上前來。
林統領這才敢奉到皇帝面前。
匣子裡果然有兩條蟲子在,且顯然並非是尋常蛀蟲。
這兩條多足蟲長約兩寸余,通皆呈現出怪異的紫,且是半明之態。而於這淡紫之中,又可見蔓延著一縷細細的殷紅之,如一條紅線貫穿蟲。
隨著匣子被打開,兩條蟲子似被這突如其來的亮所驚擾,在匣中飛快地遊走著。
人見得反常怪異之,無分大小,總會生出莫名的不適之——這兩條蟲子便是如此。
不知想到了什麼,鄭太醫眼底掀起了波瀾。
“鄭太醫可識得此蟲?”昭真帝微皺著眉問道:“是否為何種毒?”
行軍打仗在外,皆知異者多乃毒,輕易不可。
“臣才疏學淺,未曾見過此,實在不敢貿然下定論……”鄭太醫的面著異樣的鄭重:“或許羅太醫能為陛下解……”
羅太醫乃喬必應喬太醫的徒,這些年來在宮中雖隻同貓貓狗狗打道,但真正論起識毒解毒的本領,他多數都還是從羅太醫那裡學來的皮。
“來人。”昭真帝吩咐道:“使人前去請許姑娘和邊的阿葵姑娘前來——”
羅太醫此番並未隨扈前來,或許該讓昭昭來看一看。
監領命前去請人。
看著那隻暫時被重新合上的匣子,永嘉公主皺了皺眉。
不就是兩隻蟲子麼,為何從母后到父皇,再到鄭太醫,皆是這樣一副神態?
尤其是母親,無論東西是不是的,怎就至於為了條蟲子嚇這樣?
再看向自過來便一直跪在那裡的掌事嬤嬤,忍不住問道:“父皇,母后,到底發生了何事?”
鄭太醫等人垂著眼睛心複雜。
這要皇上和皇后如何回答?
難道要告訴公主……皇后在房中的香爐裡藏了催藥?
而就在此時,監來稟,道是太子到了。
隨著年人一同而來的,還有幾名緝事衛。
謝無恙走進堂中,掃了一眼堂的形,並未多說多問,隻行禮道:“父皇,驚馬之事有進展了。”
永嘉公主聞聲形一僵。
那原本稱得上清朗悅耳的聲音就在邊響起:“緝事衛已在北苑的湖邊發現了羊躑躅,看管馬廄的監已將有可能接到馬匹的有關之人名單悉數列出——這半日在兒臣帶人查實排除之下,可知當下嫌疑最大之人,乃是永嘉公主邊的一名名喚冬芝的侍。”
永嘉公主赫然瞪大了雙眸。
大半時辰之前,那群緝事衛在的住搜查了一番之後毫無所得,便以為不會再出差池了——然而認為的風平浪靜之下,實則卻是已經暗中查到了的頭上來了?!
冬芝那個廢,被人盯上了竟還全然不知!
“這……這不可能!”連忙道:“兄長定是誤會了什麼!”
謝無恙並不看,隻道:“那名看管馬廄的監和侍此時已候在院外——”
昭真帝的心更沉了幾分,立時道:“傳進來對質。”
立時便有緝事衛將二人帶了進來。
看著跪下的侍,海氏一顆心撲通狂跳。
果真是冬芝……
難道今日驚馬之事,竟是——
猛地轉頭看向兒。
掌事嬤嬤更是在心中苦連天——今日之事已是足夠棘手了,一波尚且未平,竟又迎面拍來了一記巨浪!
“今日天未明之時,便是這位姑娘來到了馬廄之中,說是怕公主的馬吃不慣行宮中的草料,特親自來喂……”那監有些不安地複述道。
公主邊的人來喂馬,他豈敢阻攔?
想著貴人們金貴,貴人的馬也金貴,彼時他便也不曾多想什麼。便是今日太子殿下親自來查問接馬匹之人,他也只是如實道出,而不曾懷疑到這位侍上……直到一查再查,其他人皆排除了嫌疑,竟獨獨剩下了這侍嫌疑最大!
經查實,那發現了羊躑躅的湖邊小徑,便是自馬廄返回永嘉公主住的必經之路!
如此之下,他難免就有些自危了,此時半點也不敢抬頭去看一旁的永嘉公主。
“可有此事?”昭真帝看著冬芝問道。
他和將軍一樣,多是將疑心放在了各方勢力之上,將此次驚馬之事認定為朝堂之爭——
可阿淵既是將人帶到了他的面前,便足以說明至有了七把握。
若果真如此,倒是他低估了小兒家的心思之重。
但錯便是錯,兒家也同樣要承擔後果,縱然當真就是桑兒所為,他也絕不會有半分包庇——
“是……婢子的確去過馬廄!但婢子只是替公主殿下喂馬而已,本不曾做過其它!更加沒有過許姑娘的馬!”冬芝將頭在地上,聲音堅定而委屈:“請陛下明鑒!”
“荒謬!本宮何時讓你去喂過馬?難怪今早起時未見到你,原來竟是打著我的幌子去了馬廄!”永嘉公主驚怒道:“說,你究竟是了何人收買指使?竟妄圖將這髒水往本宮上潑!”
額頭抵著地磚的冬芝臉上頓時爬滿不可置信之,渾也於一瞬間變得冰冷僵。
公主這是在幹什麼?
便是公主承認今日讓去過馬廄又如何?誰又能證明那羊躑躅就是扔的?毒就是下的?
可公主仍是想也不想便推翻了的話!
這是公主不夠聰明,被嚇得慌了神嗎?
不……
公主這是怕再有其它證據出現,所以乾脆從一開始便否認讓去過馬廄的事實,以此將推出去頂罪來了結此事,直接切斷一切對自不利的後患!
見跪在那裡的人沒有反駁,永嘉公主心下稍安,遂又道:“父皇有所不知,自冬芝隨我來了京師之後,便多有反常之舉,起初我還隻當是不適應宮中生活……現下看來,還不知是起了什麼心思,暗中同什麼人勾結上了!此事您可得人細查才好!”
當然知道單憑這幾句話,不足以父皇全信。
但此時這麼多外人在,的面便是父皇的面,父皇如何也不可能直接將這罪名定在的上!
至於冬芝——
主子犯錯,下人頂罪再尋常不過,下人不就是拿來用的嗎?
若對方識趣些,自是知道該怎麼說,若是不識趣……呵,只要父皇有意在明面上遮下此事,隨對方怎麼說也不過都是些狡辯汙蔑之辭罷了!
想著這些,永嘉公主半點懼意也無,大不了是被父皇私下責備幾句罷了。
不料,卻聽昭真帝向冬芝問道:“你果真是收了他人收買?”
永嘉公主怔了怔。
隻管將人拉下去“審問”便是了,父皇作何還要這般問?
而此時,堂外有宮人的行禮聲傳了進來。
“太后娘娘,許姑娘……”
許明意今晚一直在太后,監前去尋人時,太后聽聞了此發生的事,不免也一同過來了。
聽得堂中正在查實驚馬之事,太后並未多說,隻由許明意扶著在堂中坐下,輕輕拍了拍孩子的手,示意且先聽一聽。
許明意便站在太后側,靜靜看著堂中的形。
今晚之事,似乎有些複雜。
除卻與有關的這一件之外,又同時發生了其它要之事。
此時對於海氏,心底不免有些疑,但同時亦有一種直覺——這些疑,或許很快便能得到解答。
只是還須一件件地聽,一件件地看。
視線中,那綠侍緩慢地抬起了頭,卻是定定地看向永嘉公主——
“婢子從小陪著公主一同長大,公主京之後,婢子也了旁人眼中風面的大宮,如此之下,試問何人會想到要來收買婢子?何人又能收買得了婢子?若非是公主之命不可違,婢子又豈會冒著命危險去害未來太子妃!”
永嘉公主臉一變:“你……果然是衝著汙蔑本宮來的!”
這個賤婢,竟然還敢多言多語,是怕死的會太輕松嗎!
“公主無非是讓婢子頂罪罷了。”綠侍滿眼悲恨地笑了一聲,道:“公主於玉粹宮中打殺宮人已是家常便飯,如今只是到婢子送命了而已……”
察覺到昭真帝的視線看了過來,永嘉公主面微白,大怒道:“休要再胡言汙蔑本宮!”
看著那雙怨恨報復的眼睛,心底忽升起極不好的預來,正要擅自做主吩咐監將人拖下去時,卻已聽對方說道:“公主不是一貫自詡敢作敢當嗎?怎此時卻連承認的膽量都沒有了?既公主不敢說,那便由婢子替公主來說好了……公主對太子殿下心存慕,因此百般針對嫉恨許姑娘,故設計了驚馬之事!聲稱要給許姑娘一個教訓,縱然不能要了其命,稍毀了樣貌摔斷了也是不能再做太子妃的!——這可是公主的原話!”
四下眾人紛紛變。
這……這又是什麼?!
這也是他們能聽的嗎?!
前有皇后圖給皇上下催藥……
現又出了個——
驚!堂堂公主殿下之所以對未來太子妃狠下毒手,原因竟是這個!
“……”海氏震驚地看向兒。
桑兒……慕太子?!
怎麼可能!
海氏腦中嗡嗡作響,僅存的一理智讓從一件件小事中找出了痕跡所在。
怪不得……
怪不得這份“懂事”來得如此反常,原來竟是……
太后眉心皺,卻也不見喝止冬芝之意——出了醜事便不要怕丟人,試圖遮遮掩掩,遮到最後,醜事怕是要釀禍事。
更何況,他們謝家需要給遭了這場無妄之災的昭昭一個完整的待。
“胡說八道!”永嘉公主的臉不停地變幻著,憤,不安,及無法言說的未知恐懼,讓幾乎失了態,當下就要朝冬芝撲過去:“我看你是瘋了!”
“夠了!”昭真帝臉微沉:“將人帶下去——”
是非真假,他心中已有判斷。
“父皇……”冬芝很快被押了下去,永嘉公主還再說,卻被昭真帝冷聲打斷:“你也退下。”
看著那張出冷意的側臉,永嘉公主張了張,心中升起畏懼來。
父皇似乎是真的怒了,還從未見過父皇這般神態……
手足無措地在原站了片刻,到底是咬應了聲“是”,退了出去。
但未曾離開,也不敢就此離開,而是站在了堂外。
聽得堂傳來父皇慚愧而鄭重的聲音——
“此事是我教無方,險些鑄大禍,待回京之後,必會給許姑娘一個完整的待。”
永嘉公主握了冰涼的十指。
父皇這就當眾定下了的罪名嗎?!
回京之後……
回京之後,父皇打算如何置?!
不過只是想教訓一下許明意……可是公主,父皇的親生兒,唯一的兒!
堂中的說話聲還在繼續。
“只是當下還有一個忙,尚需許姑娘相幫。”
許明意會意:“是,阿葵——”
前去尋的監已將大致形說明,阿葵也大致有了準備。
且這準備是有足夠的本領作為支撐的——這些日子以來,小丫頭一直在為自家姑娘說出去的大話而努力著。
正如“有些面戴得久了便摘不下來了”,同理,有些鍋背著背著,也就變自己的東西了——背鍋的最高境界,莫過於此。
饒是如此, 神醫阿葵在瞧見那兩條蟲子時,仍舊未能做到冷靜對待,頗為驚詫地道:“這……這似乎是蠱蟲!”
在裘神醫那本不外傳的醫書裡看過的!
蠱蟲?!
堂中眾人面驚變。
雖多數人不知為何,但一聽這個“蠱”字,已足夠人膽寒了!
歷朝歷代,巫蠱之皆被視為大忌,當朝亦不例外!
鄭太醫雖是已有預料,但真正聽到,仍是難掩驚,忍不住向側的小丫頭詢問道:“聽聞蠱蟲分許多種,用途也各不相同,不知這兩條是……”
阿葵猶豫了一下,但轉瞬想到來時姑娘的待:‘無論待會兒看到了什麼,都只需據實而言。’
便如實道:“像是蠱……”
猜你喜歡
-
完結282 章
傲嬌醫妃
她是醫學界的天才,異世重生。兇險萬分的神秘空間,低調纔是王道,她選擇扮豬吃老虎翻身逆襲。他評價她:“你看起來人畜無害,實則骨子裡盡是毀滅因子!”她無辜地眨著澄澈流光的眸子,“謝王爺誇獎,只是小女子我素來安分守己,王爺可莫要聽信了讒言毀妾身清譽!”錯惹未婚夫,情招多情王爺,闊氣太子與帥氣將軍黏上來……美男雲集,
74.4萬字8 78135 -
完結539 章

世子爺他不可能懼內
顧淮之救駕遇刺,死裡脫險後染上惡疾。夢中有女子的嗓音怯怯喚著淮郎。此等魔怔之事愈發頻繁。 顧淮之的臉也一天比一天黑。 直到花朝節上,阮家姑娘不慎將墨汁灑在他的外袍上,闖禍後小臉煞白,戰戰兢兢:“請世子安。” 嬌柔的嗓音,與夢境如出一轍。 他神色一怔,夜夜聲音帶來的煩躁在此刻終於找到突破口,他捏起女子白如玉的下巴,冷淡一笑:“阮姑娘?” ……
89.2萬字8.18 15272 -
完結105 章

盲妾如她
俞姝眼盲那幾年,與哥哥走散,被賣進定國公府給詹五爺做妾。詹司柏詹五爺只有一妻,伉儷情深,因而十分排斥妾室。但他夫妻久無子嗣,只能讓俞姝這個盲妾生子。他極為嚴厲,令俞姝謹守身份,不可逾越半分。連每晚事后,都讓俞姝當即離去,不可停留。這樣也沒什…
49.6萬字8 28902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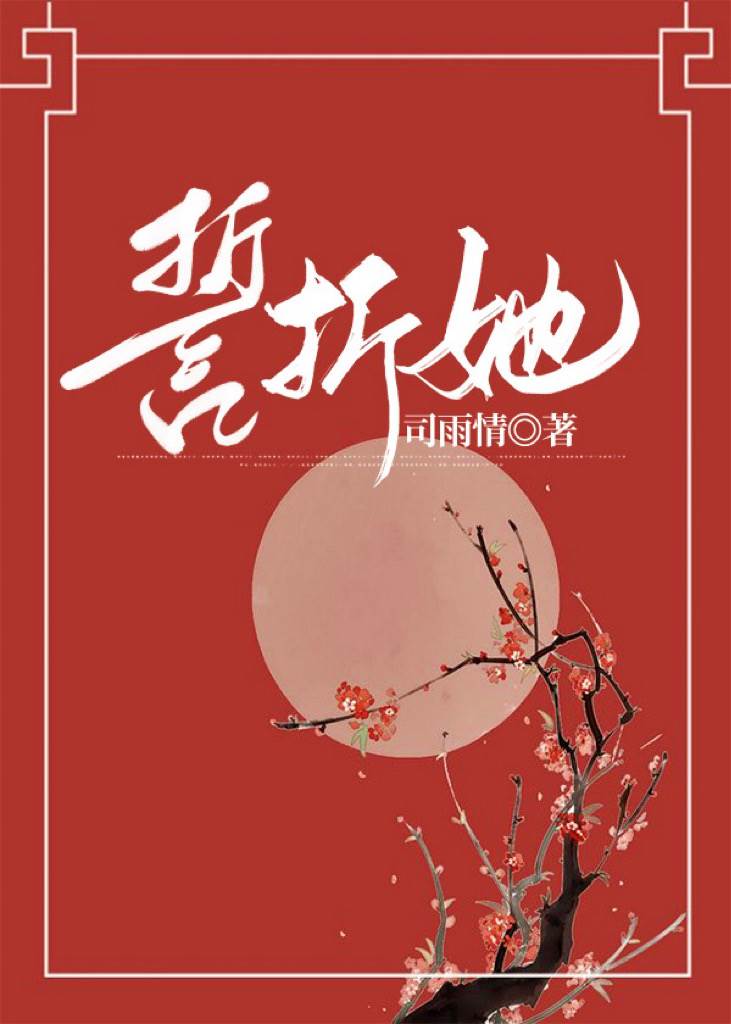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6818 -
完結587 章

戰神重生,王妃帶著醫術炸翻王府
堂堂大夏國掌政帝姬,重生到相府不受寵的嫡長女身上。被逼著嫁給一個瘸腿不受寵的王爺,想要不動聲色除了她?姐姐一門心思的想要弄死她?很好,她難不成是小白兔,任由這群人欺負嗎?想要弄死她,那也得看看有多大的本事。本想逃離王府,計劃復仇,卻沒想到,被那瘸了雙腿的夫君抱起,苦苦追求,愛她入骨。她要報仇,他為妻善后。她要殺人,他為妻磨刀。她要打胎,他雙眼含淚,跪在地上祈求不要!
103.1萬字8 34673 -
完結339 章

王爺每日一問,小妾今天宅鬥了嗎(九重錦)
宅鬥,非雙潔被壓製了十幾年的庶女,一朝被重新安排了命運,入了王府,助長了她的野心。生父的漠視,任由嫡母欺淩她們母女半生,從不庇護半分。嫡姐以為,她是個空有美貌的草包美人,想利用她的美色為自己固寵。卻不曾想,她脫離了所有人的掌控。為了往上爬,她也用盡手段,沉浮在虛虛實實的感情裏,直到她徹底認清現實,這一切的人和事都在教她如何做一個立於不敗之地的女人。
60.8萬字8 2191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