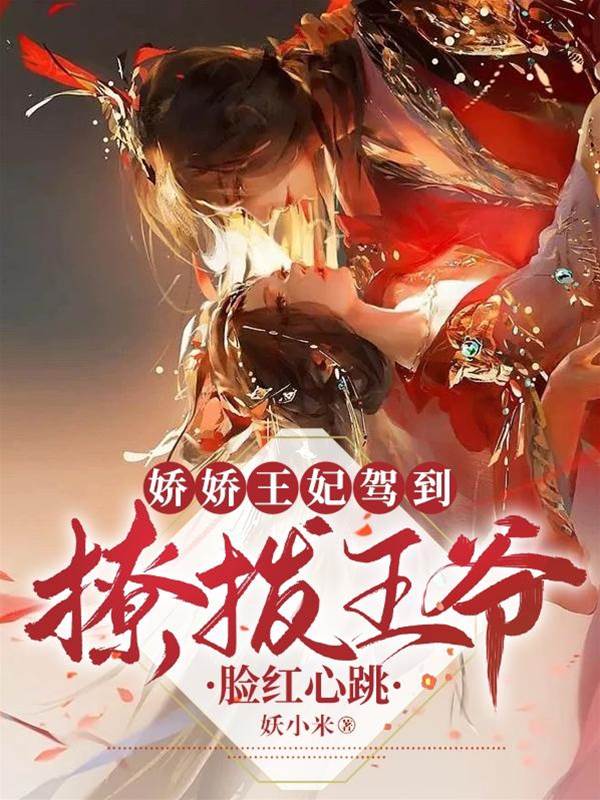《鹿門歌》 第70章
平煜萬沒想到林之誠輕功如此出神化,明明剛纔琴聲還在一丈之外,眨眼工夫便已如鬼魅般追至後。
擡眼往前一看,發現他們所在之早已越過樹林邊界,地勢微凹,正位於林旁的一山坳中。
這地方極蔽,林中之人若非按圖索驥,斷難發現此藏有陣眼,顯見得林之誠在原有陣法基礎上做了改,
恰好風聲刮來,送來一點輕微的靜,他百忙之中凝神一聽,心中一定,猛的將傅蘭芽推遠,斷喝道:“快跑!”
與此同時,察覺後之人已撲抓向他肩頭,忙作勢掉轉手中刀鋒往後刺去,不等招式用老,左手卻不易察覺一抖,變出一把雪亮匕首。
傅蘭芽被推得一趔趄,倉皇回頭一,見有人已如靈猴一般從中一竄沖天,招式說不出的怪異迅猛,心知正是林之誠本人,雖不懂武功,但單看這架勢,手也斷非常人能比。
勢危急,繼續留在原地於事無補,來不及再看平煜的形,忙手腳並用朝山坡上爬去。
出了這山坳,便是樹林,爲免平煜傷,要在最快速度通知旁人,越快越好!
聽得後兵刃相接,搏鬥激烈,一時間擔心到無以復加,卻起心腸,頭也不敢回,用最快速度爬上山坡,奔了一段路,擡頭見前方林中有人急奔而過,似是聽到召喚,往旁而去,忙張喊,卻發現自己依然口不能言。
心急如焚,四下裡一顧,蹲下撿起一塊石頭,使出最大力氣揮胳膊,往前擲去。
誰知剛一揚臂,就聽林中傳來紛雜的腳步聲,接著,就聽李攸焦躁無比道:“再找不到他們,乾脆把這地底下的坑坑窪窪一把火都燒了得了!“
秦晏殊急聲道:“點火豈不會誤傷到傅小姐?還是按洪幫主說的法子,一個一個排查生門,時間尚短,平大人和傅小姐多半還在林中。”
傅蘭芽聽得再明白不過,大喜,忙丟下手中石頭,往前奔去。
片刻,李攸、洪震霆及秦晏殊姐弟率領一衆人等出現在眼前,驟然見到迎面奔來一人,先是戒備地停下腳步,等看清是傅蘭芽,秦晏殊面一鬆,第一個迎上前,大喜道:“傅小姐!”
李攸和秦勇一怔,忙也大步趕至旁,臉上都有焦急之,齊齊出聲。
“平煜呢?”
“平大人呢?”
傅蘭芽顧不上奇怪秦勇的神和語氣,衝衆人點點頭,急惶地指指後,掉轉,引著衆人往來路走。
“你被點了啞?”秦勇發現不對勁,急追兩步,替傅蘭芽解了。
傅蘭芽大口氣,只覺頭仍堵著一團棉花般,說不出的哽噎難,啞著嗓子道:“平大人帶我從陣中逃出後,被林之誠追上,現下二人已上手,就在前方的山坳中。”
衆人大驚。
諸錦衛都知道這位南星派掌門人武功都多了得,聽得平煜孤軍戰,面一變,齊刷刷拔出繡春刀,一言不發奔向山坳。
尤其是陳爾升,雖然反應稍慢,又素來寡言,此時越發悶頭不響,一張臉憋得通紅,轉眼便追上李珉,牛犢一般跑在最前方。
洪震霆聽得多年老朋友再次面,怔了一下,隨即長嘯一聲,越過衆人,如飛鷂般往前而去。
秦晏殊雖然極想將傅蘭芽單獨帶離此,卻也不願讓平煜陷險境,猶豫了片刻,拔劍跟上。
只暗想著,一會無論如何要看好傅蘭芽,不能讓被人趁擄走。
傅蘭芽滿心都只有平煜,對諸人心思無暇揣測,只恨自己跑得不快,一時未注意腳下,一不小心絆到角,跌倒在地。
顧不上疼,忙要爬起,卻有人已提著的胳膊,將扶起。
傅蘭芽自覺此人力量極大,作卻溫,擡頭一看,卻是秦勇。
秦勇臉蒼白,似是頗爲擔憂南星派不好應對,扶起傅蘭芽,衝勉強一笑,又往前而去。
傅蘭芽心知以的功夫早已可將自己遠遠甩開,卻仍時刻不忘關照自己,心中激,強著滿腔憂心,低聲道:“多謝。”
行了一段,還未到山坳,便聽到激烈過招聲,傅蘭芽不知平煜是否在林之誠手下吃虧,心頓時高高提起,忽聽一聲悶哼,不知是誰了傷,忙要急奔幾步,便見山坳中有人已一躍而起,落到一旁地上,趔趄了幾步,到底穩穩站住。
衆人定睛一看,正是平煜。
恰在此時,山坳中有一著玄的男子跟在平煜後一衝而出,片刻不讓,屈爪朝他抓去。
而他後,壎聲齊齊響起,原來是南星派的弟子已經彙集在一,正紛紛從陣眼中奔涌而出。
平煜哪等林之誠欺至跟前,咬牙翻往後一躍,生生拔地而起,幾下竄上後樹梢,而洪震霆不等林之誠使出下一招,早已橫刺裡斜縱躍出,抓向林之誠肩頭。
林之誠聽得後拳風渾厚,顧不上再對付平煜,轉而跟洪震霆起手來。
平煜在樹梢辨認一番底下形,順了順口繁的氣息,從樹梢上一躍而下,朝傅蘭芽奔來。
李攸等人心知平煜跟林之誠纏鬥這許多功夫,斷不可能未傷,忙要去至平煜邊,不料剛跑兩步,南星派弟子已從山坳中殺將而出,衆人頓時被絆住手腳,只得撇下平煜,持劍相迎。
傅蘭芽落在衆人後,離山坳尚遠,未所擾,迎到平煜邊,仰頭看他,見他脣邊有,心頭一慌,一時忘了在旁人面前掩飾,忙從袖中取出絹帕,踮腳替他拭,又急聲問:“到底傷到了何?是不是很難?”
平煜不聲一掃,衆人都忙於對付南星派,獨有秦晏殊百忙之中不時看傅蘭芽一眼,見狀,臉上似乎帶著困之,連眉頭都蹙了起來。
平煜一點也不想傅蘭芽被人議論行止,忙不聲將傅蘭芽擋住,接過手中絹帕,了兩把道:“無事。”
只覺那絹帕上香氣清甜幽暖,縷縷沁鼻端,跟上香味如出一轍,著著,心中靈乍現,滯了一下,正要確認似的看向傅蘭芽,斜刺裡卻殺過來一人,平煜只覺那人招式平平,將傅蘭芽護在後,擡便朝那人當踢去。
須臾,又有不人前赴後繼涌到他邊,目標直指傅蘭芽。
平煜雖然了傷,對付這些鼠輩卻不在話下,手起刀落,殺得極輕鬆。
忽然間,琴聲大起,二人擡頭一,卻見林之誠不知何時已盤穩穩坐於一株參天大樹上,形巍巍,低眉斂目起琴來。
傅蘭芽頭一回得以仔細打量林之誠,見他穿玄袍,約莫五十許人,氣度高華,眉目朗疏,看得出年輕時定有一副好皮囊,可此時神卻說不出的鬱。
再一打量,卻見他上一前一後揹著兩個鼓鼓囊囊的包袱,裡頭不知裝著何。
看了又看,想起那晚洪幫主所說,忍不住悚然地蹙眉,難道那包袱裡真裝著他兩個孩兒的骨?
說起來也是費解,他兩個孩兒已經夭亡二十餘年,他日日將他們的骨放在旁做何用?他如此執著,難道那藥引一說,當真有起死回生之效?
思忖一番,想起一事,甚覺不解,林之誠消二十年,他那位溫賢淑的夫人又在何?林之誠如此捨不得他的一雙孩兒,想來當年跟夫人必然極深厚,爲何這些年他只一心要復活孩兒,邊從未有過他夫人的蹤影?
正想著,那琴聲如流水般傾瀉而下,曲子卻從未聽過,只覺曲調說不出的哀怨悲悽,聲聲慢慢,直抵人心。
平煜聽在耳裡,卻是另一番景,只覺那琴聲如利刃一般,將他原本被洪震霆護住的形盔甲撬開一條,琴聲蘊含的無數針順著那條直扎過來。
看得出來,林之誠已經耐告罄,眼下已做了破釜沉舟的準備,將全部立傾注在這一曲上,務求在最短時間力克衆人。
平煜本就已了傷,一時支撐不住,形一晃,後退一步,看清形勢,揚聲道:“這曲子不對勁,那心法恐怕支撐不了多時候,需得速戰速決。”
李珉和陳爾升等人頓時想起在別院時商議好的圍剿林之誠的法子,忙極有默契一對眼,留下一半人馬在原地對付南星派散在弟子,剩下諸人,則紛紛縱上樹梢,前後包抄殺向林之誠。
誰知越離得近,那琴聲越發刺耳,中氣息被這琴聲挑得如同沸水般滾起來,本無法調順。
平煜見狀,本打算躍上樹梢幫洪震霆解困,可一想到之前傅蘭芽掉落陷阱的形,走開兩步,又停下,無論如何也不肯留一人在此,又放心不下旁人,只喝道:“不用管旁人,只需速速幫洪幫主解困便可。”
恰在此時,李攸及一干人等終於極力抵住那琴聲,幫洪震霆甩開那幾名南星派長老。
洪震霆心無旁騖,幾下縱至林之誠前,化拳爲掌,頂著那聲聲挑心絃的巨大聲浪,朝林之誠前劈去。
林之誠忙豎起那柄琴擋住來勢,又往後一掠,與洪震霆拉開距離。
可秦勇及白長老等人早已從後頭包抄而來,劍氣一漲,向林之誠。
東西兩側,則是洪震霆的門下高手及行意宗的李由儉等人。
林之誠見琴聲已無法克敵,索將琴拋下,目一掃,忽然面一冷,輕飄飄擊出一掌,直指衆人中力稍弱的餘長老。
可衆人早已在別院中研究了林之誠慣用招,只作出未識破他伎倆的模樣,然而不等他欺到餘長老前,便四人合力,使出一招八卦游龍掌,給予林之誠背後重重一擊。
這一招集合了四人力,可謂滔天巨浪,林之誠哪怕力再了得,一時也招架不住,只覺心脈都有被震斷之嫌,連力都無法繼續維繼,不慎從樹梢跌落。
他懷中不知何,隨著他下落之勢跌出,正好落在傅蘭芽腳下。
平煜怕那東西有詐,不等傅蘭芽俯,便搶先撿到手中,展開一看,卻是一幅畫卷。上面畫著一名中年男子,面白無鬚,長眉鬢,頗爲。
傅蘭芽在一旁看見,一震,失聲道:“我見過這人!”
平煜一眼便認出畫上所畫之人是王令,忽然想到其中關鍵,心裡生出一個猜測,凝眉不語。
傅蘭芽卻又道:“平大人,你可還記得那回在六安客棧時,我曾跟你提起過,那客棧中的佈局跟京城流杯苑的格局極像,而畫像上這人,正好是我當年我哥哥帶我去流杯苑聽曲時在外頭撞見的。我記得這個人當時看了我許久,眼神又頗奇怪,故而印象深刻——”
平煜怕傅蘭芽想通其中要,心中涌起濃濃憂,不等再往下說,將那畫卷收起,只道:“世上長得相似之人不,許是你記錯了也未可知。”
作者有話要說:本來這一更想寫6000多字再發,看大家催的厲害,先發一半上來
猜你喜歡
-
完結1055 章

侯府小啞女
燕云歌自末世而來,重生侯府,她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每天吃好喝好樂無憂!然而……她爹一門心思造反,她哥一門心思造反,她嫁個男人,還是一門心思造反。燕云歌掀桌子,這日子沒發過了!
272.1萬字8 16626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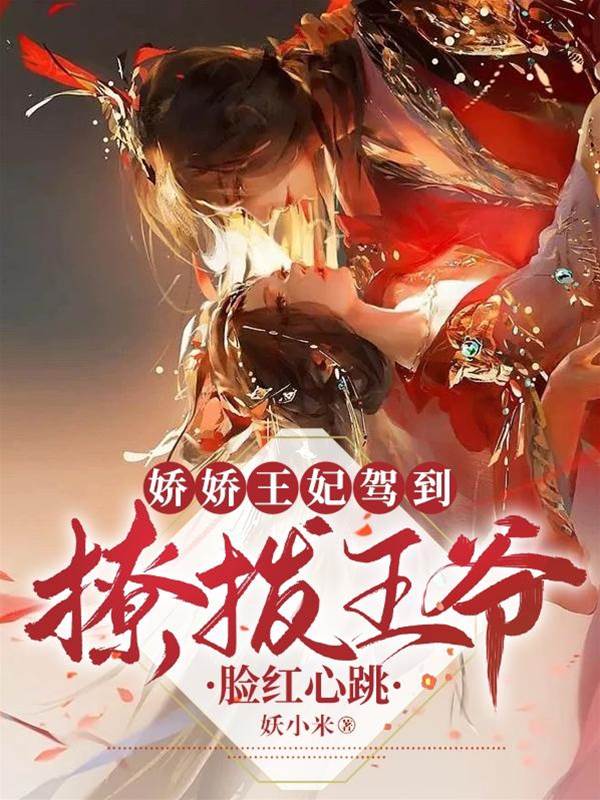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1760 -
完結372 章

穿成短命白月光后,和反派HE了
桑遠遠穿進一本古早玄幻虐戀小說裏,成了男主那個紅顏薄命的早逝白月光。男主愛她,男配們也愛她。女主因爲長了一張酷似她的臉,被衆男又愛又虐又踩,傷身又傷心。和男主的感情更是波折重重狗血不斷,虐得死去活來,結局還能幸福HE。桑遠遠:“不好意思本人一不想死二受不得虐,所以我選擇跟反派走。打擾,告辭。”反派長眸微眯,姿態慵懶,脣角笑意如春風般和煦——“我的身邊……可是地獄呢。”她沉思三秒。“地獄有土嗎?”“……有腐地。”“有水嗎?”“……只有血。”他想看她驚惶失措,想等她尖叫逃離,不料女子呆滯三秒之後,雙眼竟然隱隱放光——“正好試試新品種!”“……”他在最深沉的黑暗中苟延殘喘,從來也沒想到,竟有一個人,能把花草種滿一片荒蕪。
57.1萬字7.92 9667 -
完結313 章
亡國后成了反賊的寵婢
姜嶠女扮男裝當了幾年暴君。叛軍攻入皇城時,她麻溜地收拾行李,縱火死遁,可陰差陽錯,她竟被當成樂伎,獻給了叛軍首領霍奚舟。姜嶠捂緊馬甲,計劃著再次逃跑。誰料傳聞中陰煞狠厲、不近女色的霍大將軍竟為她破了例。紅燭帳暖,男人摩挲著她眼角的淚痣,眸色暗沉,微有醉意,“今夜留下。”*姜嶠知道,霍奚舟待她特殊,只是因為她那雙眼睛肖似故人。無妨,他拿她當替身,她利用他逃命。兩人各有所圖,也是樁不虧的買賣。直到霍奚舟看她的眼神越來越深情,還鄭重其事地為允諾要娶她為妻,姜嶠才意識到,自己好像是在作繭自縛——
49.2萬字8 68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