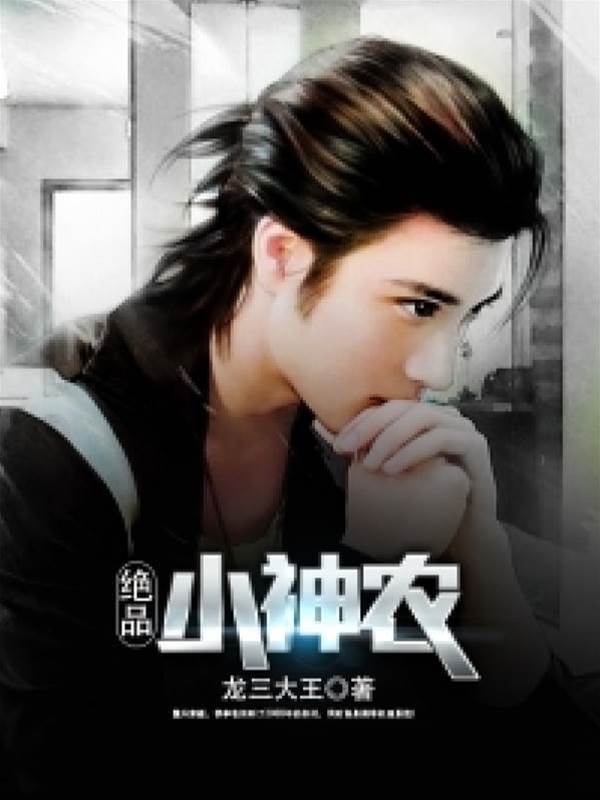《太子妃升職記》 第 74 章
案子查完了,剩下的就是怎麼判了。
楊豫雖有人命在,可他也有軍功,最後判了個削爵奪券,一家子給遷去了嶺南。
茅廁君由楚王降爲郡王,罰了三年的薪俸。
至於張翎那裡,更好說了,直接從軍中開除,永不起復。
這個結果,雖然比茅廁君預料的壞了許多些,不過倒也算是沒偏離了大方向。這一番折騰,直到來年三月,這場轟轟烈烈的“史被殺案”才落下了帷幕。
三月十二便是齊灝的一週歲生日。
由於之前的“史被殺案”牽連太廣,朝中有事沒事的大臣都跟著打了小半年的司,齊晟自己好像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就想著藉著這個機會緩和一下朝中的氣氛,便下了旨意要大辦皇長子的生日。
我其實是很喜歡這種熱鬧的,可礙於皇后的名聲,卻又不得不故作賢良地去大明宮勸齊晟要節儉,萬萬不能大大辦齊灝的生日宴。
齊晟正站在書案前臨帖,聞言只擡眼瞟了我一眼,問:“你真這樣想?”
我一貫堅持“小事上要說大實話,大事上要扯小瞎話”的原則,聞言搖了搖頭,答道:“我也想辦的熱熱鬧鬧的,最好再來個大赦天下,大夥都知道灝兒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齊晟輕輕地嗤笑了一聲,“這不就得了。”
我也跟著打了個哈哈,主地走到一旁幫他研磨,嬉笑道:“不都是爲了應付名聲嘛。我也就來這麼一趟,和你這麼一說,你聽就聽,不聽我更高興。”
齊晟停了筆,擡頭看我,過了一會兒後突然說道:“我想立灝兒爲太子。”
我聽了這話卻是真的心中一驚,想也不想地說道:“別,這事還是算了。”
齊晟仔細地打量我,問:“這是真話還是假話?”
我打算走以人的路線,正道:“你也是做過十多年太子的,你還不知道做太子的滋味嗎?若說太子妃是天下最難做的,那麼太子就是天下第二難做的,何必灝兒去這個苦。”
齊晟挑高了眉峰,“你覺得太子妃比太子還要難做?”
我對於他這種抓不住句子重點的行爲已經習慣如常了,也不理會,只是說道:“皇上眼下年青力壯,以後若是能遠酒勤鍛鍊,早睡早起勞心,估計再活個四五十年是不問題的。”
這話估計還算中聽,齊晟慢慢地點了點頭。
我又說道:“那就是說若是現在立灝兒爲太子,他這個太子就要做到四五十歲,你可見過有哪個太子能熬得過四五十年?”
齊晟靜靜地看著我,不發一言。
“他現在還太小,不知道以後會長什麼樣子,是不是真的有才能擔起這個江山。”我停了停,垂下了眼簾,才又繼續說下去,“而你又太年輕,以後還會有越來越多的兒子,也許就會有一個比灝兒更得你的喜,到時候,你要怎麼辦?你又要灝兒怎麼辦?”
齊晟還是不說話,我沒看他,也不知道他此刻會是個什麼表,只能揣測著他的心思,然後又低聲說道:“皇家裡,父子相忌手足相殘的事從來都不,我的前半生已經見識過了,後半生不想再看到這些。”
過了許久,才聽得齊晟輕輕地嘆了口氣,說道:“我知道了。”
果然,齊灝的週歲生日雖然辦的風,卻沒有提及儲君之事。其後沒幾天,我再去大明宮的時候,就發現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一向堅守崗位任勞任怨風雨不誤十幾個月如一日的小江同學竟然不見了。
小侍湊在我邊,十分恭敬地彎著腰,小聲說道:“是皇上人送走的,奴婢也不知道到底把蘇姑娘送去了哪裡。”
這個小道消息我很是吃驚,忍不住問道:“好好的,怎麼就送走了呢?還回來嗎?”
小侍小心地瞄著我的面,說道:“奴婢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要不皇后娘娘問一下皇上?”
我問?我有什麼立場問?人家江氏又不是編制的,薪水從不在我這裡領。再說我能怎麼問?問江氏這是臨時休假還是長期退?有補償金沒?以後還給三險一金嗎?
一旁的小侍還用眼角瞄著我,我隨意點了點頭,待見到齊晟的時候,卻裝作不知道這事一般,提也沒提。
齊晟也沒提這件事,只是說道:“灝兒以後漸漸大了,不能他長於婦人之手,從明日起,每日裡你都帶他過來,我要親自教養他。”
齊晟這種“教育要從娃娃抓起”的想法是好的,可做法卻有些人不敢茍同,人家上個兒園還得滿了三週歲才收呢,你就一個剛滿週歲的小娃娃每日裡過來學習政務?
我有些哭笑不得,可他說的十分認真,不帶毫玩笑模樣,只能點頭應下了。
第二日,齊晟果真就派了小侍來興聖宮催我。我沒法子,只能著頭皮抱著齊灝去大明宮點卯。
齊晟接見朝臣的時候,我就抱著孩子在屏風後聽著。他批閱奏摺的時候,我抱著孩子在榻上坐著陪著。
剛開始的時候,齊灝不悉這個環境,表現的十分乖巧,就老實地在我懷裡坐著。可沒兩天,他就再不肯老實地坐在我懷裡了,非要擰著小子下來,然後踉踉蹌蹌地往屏風外面跑。
齊晟正在外面聽吏部、戶部的幾位員奏事,我哪裡敢他跑出去,只能拎著他的領把他扯了回來。誰知這下可惹了大禍了,齊灝瞪了我片刻,委屈地撇了撇,下一秒就放聲大哭起來。
我這裡怎麼哄也哄不住,正急得滿頭大汗,恨不得用手去堵他的的時候,齊晟就從屏風前繞了過來,把他抱了出去,一面放在膝上輕聲地哄著,一面神自如地吩咐戶部尚書接著說。
我還坐在屏風後,外面衆人是什麼表看不真切,不過戶部尚書說話明顯不像剛纔那麼順溜了。
再後來,事就漸漸變了齊晟抱著孩子在屏風外接見朝臣,我獨自一人在屏風後認真聽講。頭兩回的時候,朝臣們還都有些驚愕,漸漸地,也就都淡定了。
這般月餘的時間過去,齊灝長沒長見識我不知道,我卻是把朝中一些事務都聽了。齊晟偶爾犯懶的時候,我都幫著他念摺子了。雖然斷句還是不太利索,不過齊晟大都能聽明白,然後閉著眼念出批覆來。
我就手抓筆,在紙條上歪歪扭扭地記下來,然後夾奏摺裡,等著齊晟自己再謄一遍。
齊晟第一次看到我寫的字時候,半晌沒說話,然後指著紙條面無表地問我:“你這是寫得什麼?”
我一時不知道他是嘲笑我字寫的爛,還是不認識這些簡筆字,想了想,才答道:“這簡筆字,是你們用的繁字的簡化,你不覺得這樣的字更簡單易學嗎?”
齊晟仔細地看了看我寫的字,不置可否,卻是說道:“以後別寫這樣的字,人看到了不好。”
我點頭應了,可等下一次寫的時候,還是下意識地就寫了簡字。
如此幾次,齊晟便怒了,也不在榻上躺著了,起走到我邊親自監督著我。
我抓著筆立在那裡,筆尖上的墨都滴下來了,也沒能寫出一個字來。
齊晟斜著眼瞥我,問:“怎麼了?”
我腦門子上都冒汗了,吭哧半天,十分不好意思地答道:“不會寫。”
齊晟納悶:“不會寫什麼?”
我了把汗,答:“繁字,沒學過,不會。”
齊晟詫異地看著我:“你剛纔讀得時候不是都認識嗎?”
我答:“看著模樣都覺得眼,就蒙著唸了,秀才認字認半邊嘛!”
齊晟看著我,終於無語了。
從那以後,我就又多了一個活,齊晟坐著批摺子的時候,我就在一旁站著練大字。如此以來,我每日裡大部分時間都要待在大明宮,有的時候齊晟政務繁忙,我還要跟著一同加班到深夜,順便也就宿在大明宮了。
我初步算了一算,自己眼下除了擔著後宮大總管的差事,還幹著機要書與生活助理的活,時不時地還要陪一陪睡……我這也算是兼數職了。
勞累之餘,我越發地思念起江氏來,想江同學可真是個有追求有最理想,踏實肯幹的好同志,若是還在大明宮的話,齊晟許就不會這樣把我當牲口使了。
五月裡,來自江北的奏報忽地多了起來,大部分都是來自軍中。我約覺到齊晟對北漠手的時間快到了。
一日,我陪著他加班到了深夜,待又牀上和他做了一番力活之後,這才趁其不備地說道:“我想回興聖宮。”
齊晟氣息還有些不穩,過了片刻才問道:“爲什麼?”
我用薄被掩住了口,擡起來看他,答道:“因爲我是皇后啊,得統領六宮啊,整日裡待在前朝算什麼事?昨日裡黃氏與李氏因爲兩匹布吵起來了,想找我評理呢,結果被人攔在大明宮外愣是沒進來。兩人轉又哭著去了太后那裡,這才把布分利索了。”
齊晟側著頭靜靜地看我,我毫不避讓地和他對視。
沒一會兒,我卻忍不住笑了出來,手推了推他,笑道:“練什麼對眼啊,帳子裡這麼黑,連個眼神都看不清,眼都白拋了!”
齊晟也悶聲笑了起來,將我拉倒在他的口上。他的膛寬厚結實,因爲在笑而微微震著,好一會兒,這震才停了下來,又過了半晌,才聽得他低聲說道:“我要去打北漠,這是祖的志。”
我不控制地一僵,腔裡的心臟卻是激烈地跳起來。爲了不被他察覺,我連忙用手撐著他的口,微微分開了兩人在一起的,著嗓子問他道:“你要親征?”
齊晟沒說話,卻把手掌輕輕地覆在我的背心。
我的心臟跳得如同擂鼓,偏生子不敢移毫,只能任他溫熱乾燥的手掌在與我的心臟只隔了一層骨的地方。
昏暗之中,約地看到齊晟的角好似輕輕地勾了勾,隨後緩緩說道:“別怕,萬一我回不來了,你就扶持著灝兒登基,正好全了你做太后的念頭。”
明明是玩笑似的語氣,可這短短十多個字,卻字字都似悶雷一般炸在了我的心頭上。我的心臟還沒出息地擂著鼓,大腦上的每一弦卻都是繃了鋼線一般,下意識地乾嚥了一口吐沫,就琢磨著得說出幾句什麼來好好表白我的忠心。
黑暗中,他的視線像是無形的利劍,簡直能直接穿人的靈魂。
我張了半天也沒能出聲。
他說這話顯然不是臨時起意,那之前我大明宮陪他理政務,算是試探,還是崗前培訓?
而他現在又需要我什麼樣的答案?
這樣思考著,激烈的心跳卻是漸漸地平復了下來,我鎮定地問道:“若是老九不服怎麼辦?”
齊晟輕巧巧地吐出一個字來:“殺。”
嗯,回答的真是一貫的言簡意賅啊!
我崇拜地看著他,驚歎道:“好主意!果然好主意!問題是……怎麼殺?”
齊晟又笑了,用手輕輕地著我後背,答道:“我幫你殺,在把權杖給你之前,我會替你把杖柄上的棘刺都除了。”
我心中莫名地一驚,面上卻強撐著笑,輕鬆說道:“嗯,不過,你可別把整權杖都給我打磨的溜溜的,那樣別人也不疼了。”
齊晟想了想,點頭:“好。”
我覺得不管他信不信,這會子怎麼也得給他煽煽纔好,於是便將頭埋進了他的懷裡,憋了半天氣後,啞聲問他道:“不能別人帶兵去嗎?”
齊晟的手順著我的脊背緩緩往上,了我的發頂,然後又用手指隨意地繞著我鬢角的一綹頭髮,輕聲答道:“沒有人比我更合適了。”
他說的倒是實話。
同祖一輩的老帥們基本上都已經被閻君請去和花酒了,就是有那麼一兩個落下的,也都七老八十指不上了。
子一輩裡,楊豫有帥才,卻不能用,張翎前一陣子剛被齊晟拉下了馬,剩下的薛家莫家之流,猛將倒是不,但是卻都挑不起主帥的擔子。
至於孫子輩上,都還太年輕,大多是孔武有餘而謀智不足,又無資歷,更不敢用。
算來算去,倒還真是齊晟自己最合適。他習兵法,有很高的軍事天分,深得祖喜,親自帶在邊教養。爺孫倆閒暇之餘除了對著沙盤推演戰法之外,時不時地還要帶著人馬去西胡草原上實踐一把,很遭草原人民的痛恨。
直到後來先皇繼位,草原人民這才過上了安生日子。
先皇是個文化人,一心只想發展經濟文化,雖然礙著祖的面子不得不立了齊晟爲太子,心中卻是不大瞧得上他這種好武的人。
齊晟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得父皇喜歡,索也就不在他眼前討人嫌,經常自請去北疆巡邊,一年裡得有七八個月在江北各個軍營裡廝混,對江北,對北漠都悉無比。
他自己爲帥親征北漠,只要別犯趙括趙大哥的病,倒是比別人都合適些。
黑暗中,兩人就這麼靜靜地躺了一會,氣氛剛有點靜謐的味道,就聽齊晟輕輕地嗤笑了一聲,問我道:“捨不得我?”
這個問題一下子把我給難住了。
我若答“不捨得”吧,估計他會不信,可我若答“捨得”吧,估計他又得不高興。我左右思量了一下,決定還是不要直接回答的好。
我從他懷裡擡起頭來,半真半假地說道:“我們兩個走到今天,連孩子都生倆了,若再說互不相干,那純屬矯得找了。你對我有防備,我對你有戒心,這很正常。信任不是靠言詞來維繫的,日久見人心纔是正理。你要去親征,我不攔你,我會好好替你守著這盛都。你回來,我還接著給你做皇后。可若是你真回不來了,我也不說那些什麼同生共死假話糊弄你,我只會好好守著葳兒和灝兒,皇位能保則保,不能保我就放手,什麼都不如活著重要。”
齊晟聽了半晌無語,終哭笑不得地嘆道:“你就這麼沒有氣節?”
“氣節?”我笑了,故意衝他臉上吹了吹氣,“我要有那東西,早吊死八百回了,現在還能和你躺一張牀上?”
這一回,齊晟沒笑,只認真地盯著我看了片刻,然後輕聲說道:“累了一天了,睡吧。”
我乖順地伏在他的懷中,心中卻在暗罵:睡個啊!今天晚上這麼刺激,大腦早興起來了,能睡著纔是怪!
過了沒一會兒,又聽得齊晟問道:“睡不著?”
我默了默,輕輕地“嗯”了一聲。
齊晟就笑道:“我也是,既然這樣,那就先別睡了,再來一次吧!”
話還未完,人已是翻覆了上來。
最初時我沒多大興致,不過轉念一想若是他真的被茅廁君長留在了江北,我這裡不得就要守寡,到時候就是再想睡個男人都不容易了。如此一想,我隨著也跟著熱起來,兩人足足折騰到快天亮,這才睡下了。
五月裡,齊晟果然宣佈要北巡。
帝王巡邊本是大事,可由於祖對北疆防務太過重視,三年兩頭就要跑一趟江北,以至於這事也沒人把它當作大事了。
到了先帝這一輩,他比較偏江南的靈山秀水,不太喜歡這種獷風格的“北疆雙騎一月遊”。無奈老爹留下來的規矩又不好破,苦捱了兩次之後靈機一換了個方式,將北巡改了皇帝出錢皇太子出力。
齊晟爲皇太子,一共代帝北巡過三次,最後一次北巡時被趙王兄弟了一把,差點在宛江翻了船。
那個時候我還是太子妃張氏,白天先拉著楊嚴橫渡了大半個宛江,夜裡又拽著楚王齊翰漂了整整一個九曲峽,搞得我後來見著活水就發憷。
這回是齊晟登基之後的第一次北巡,聲勢自是比以前做太子的時候大了不。不過除了數的幾個重臣知道他這次是借“北巡”之名行“親征”之事外,其餘的人只當齊晟又搞公費旅遊,都沒怎麼太在意,甚至還有史抨擊齊晟北巡是勞民傷財之舉。
蒼蠅雖不咬人,可它煩人啊!
我將一沓子奏摺遞給齊晟看,問他:“就不能想個法子這夥子人閉?”
齊晟隨手翻了翻就扔在了一邊,笑道:“他們他們的,你自管低著頭做自己的事就是了,管他們做什麼!”
這話說得真輕鬆啊,到時候你拍拍屁打北漠去了,還得留下我在盛都跟著這麼一幫子混。
我擡眼很是真誠地看他,商量道:“要不你乾脆帶著他們和你一起去北邊吧,閒的時候還能有幾個嘮嗑的。”
齊晟著眼皮看了我一眼,不不地說道:“不行,我這回得帶得人太多,還是給你留下吧。”
我真心覺得這事只有“不想帶”,沒有“帶不了”,你連趙王與楚王都能一塊帶上了,還怕再多出幾輛馬車給史們用嗎?
沒錯,這次“北巡”齊晟竟然命趙王和茅廁君一同侍駕。
最初聽得這個消息時,我還驚愕了那麼兩秒鐘,不過很快就理解了齊晟的用意。他對這兩個兄弟都不怎麼放心,與其留他們在盛都,還不如放自己邊看著更放心一些。
臨行前,茅廁君終於逮到機會,突破重重阻礙與我在宋太后那裡見了面,拿了一張比真的還像真的聖旨給我看。
那是以齊晟的口氣寫得詔,也可以算是罪己詔,字裡行間充沛,文采斐然,用簡單煉的文字,概括了一個皇帝因不聽羣臣勸阻執意北伐而最終導致自己死疆場的“事實”。
這一句夠長吧?看著費勁吧?你還別抱怨,這比起我看的原版聖旨來,這都是簡化版的了,我好歹還給你加了個逗號呢。
也虧得我前陣子在齊晟的威之下苦練文言文,總算是將這份聖旨看懂了個七七八八。
聖旨的最後,齊晟將皇位傳給了皇長子齊灝。
茅廁君待我看完,將聖旨從我手裡了回去,淡淡一笑,說道:“爲安全計,這東西先放在太后這裡。若是江北不能事,皇后只當自己從沒見過這樣一份東西。但若是江北事了……”
他說到這裡停了下來,目沉靜地看著我。
我笑了笑,接道:“若是你那裡事了,我就用此聖旨扶皇長子登基,然後命你與張放同朝輔政。不過,你也要多注意一下,莫要給北漠撿了便宜去,一旦他們趁機反撲過來,再要趕出去可就難了。”
茅廁君點了點頭,又鄭重說道:“我也是祖子孫,定然不會韃子過靖的,也皇后守諾。”
守諾這事吧,不能只看說的,得看做的。我沒說什麼,只對他扯了扯角,然後便起往外走。人剛走到門口,茅廁君又在後面喚住了我,等我回看過去,他卻又不肯說話,只靜靜地看著我。
我問他:“還有事?”
茅廁君卻是淺淡地笑了笑,輕輕地搖了搖頭。
我最最不得這種文藝小清新的範兒,只覺得牙都酸倒了半邊,忙轉出去了,帶著宋太后送給我的兩個小人回大明宮。
後殿裡,寫意剛指揮著宮給齊葳和齊灝兩個小祖宗洗完了澡,不亞於剛打完一場水仗,連頭髮上都還滴著水珠,聽說我回來了,忙迎了出來,關切地問我道:“娘娘,沒事吧?”
話問出了口,這纔看到我後還跟著兩個面生的小人,面上不覺出些驚訝之。
我向寫意簡單介紹了一下這兩個小人,都是宋太后遠得不能再遠的遠房親戚,明面上說是派過來伺候皇帝和皇后,暗底下卻是希我能給開個後門,把這個工作地點設定到齊晟的龍牀上。
寫意聽了直撇,等人都走了,與我說道:“奴婢還當太后請娘娘過去有什麼事,原來又是安狐子過來。要奴婢說娘娘也別和們客氣,就把人留在宮裡伺候娘娘,看們有沒有命活到皇上北巡迴來。”
那兩個小人都是十五六歲年紀,正是得跟花骨朵一般的年紀,只看著就人賞心悅目,我倒是有心把們留在自己邊,可這人畢竟是太后送的,怎麼也得和齊晟說一聲纔是。
齊晟一聽太后又送了兩個遠房親戚過來,卻是劍眉微皺,說道:“也不知這太后哪裡來得這麼多孃家人,還沒完沒了了。”
我斂目不語,心中卻想這有什麼啊,要是放到現代,轉上幾轉都能你和非洲黑猩猩攀上親戚。這好歹還都是人呢,你就知足吧。
齊晟瞥了我一眼,又問:“是兩個人?”
我真心實意地答道:“確是人,天生麗質,俏可人。”
齊晟緩緩地點了點頭。
我試探地問道:“皇上這回北巡,要不要把們帶在邊解個悶?”
齊晟搖頭,“我去打仗,帶什麼人!”
我暗中大鬆了口氣,面上卻是笑道:“也是,人家都說軍營裡不能進人的,不然不吉利,這兩個就先留在宮裡吧。”
齊晟狐疑地看了我兩眼,眉頭微皺,想了想又說道:“算了,還是帶在我邊吧,心裡更踏實些。”
皇帝開口,不敢不從,我老實地應了一聲“是”,心中卻是十分鄙視他這種反覆無常的脾氣。
猜你喜歡
-
連載262 章
快穿係統之女主是boss
(1v1甜寵,男神略微病嬌~)梵輕死了,然後莫名的繫結了一個係統。係統:你要去不同的世界扮演女主,然後………梵輕點頭:懂了係統:等等我還沒有說完!等等宿主你幹什麼!你是身嬌體軟的女主,不是反派!等等宿主那是男主,宿主快把刀放下!不,宿主那是反派,你們不能成為朋友!宿主那是惡毒女配,你們不能做交易!然後,係統就眼睜睜的看著它的宿主,一次又一次的走上人生巔峰。本書又名《我的宿主總在黑化》
27.7萬字8.18 9486 -
完結7204 章

至尊瞳術師
24世紀的至尊瞳術師一朝穿越,成了下等小國鎮國侯府被廢的天才大小姐!修為被廢,雙眼俱瞎,家族地位被奪?洛清瞳微瞇著一雙血瞳冷笑:過來!姐教你們做人!一雙血瞳,傲世無雙!鑒寶透視,醫毒破防,無所不能!魂武雙修,器藥雙絕,禦獸佈陣……她用一生詮釋了何謂至尊無雙,絕世囂張!隻是萬萬冇想到惹上了一個比她更絕世妖孽的人!
660萬字7.92 467038 -
完結220 章
我憑釀酒征服帝國[直播]
星纪6832年,人类帝国的民众深受躁狂症严重威胁,有人说,这是末时代,帝国将因为躁狂症而走向灭亡。酿酒师苏少白一朝穿越,生活所迫直播酿酒,却没成想,酿出的酒轰动了整个帝国。花瓣酒,可减轻初期躁狂症者的焦虑感。黄酒、米酒,可梳理中期躁狂症者的精神阀。药酒,可治疗重症躁狂症者的精神分裂症。一不小心,苏少白成了拯救帝国的英雄。本文讲述的是一位现代酿酒师苏少白穿到星际时代的故事,他在无意间得知人类帝国几百亿民众深受躁狂症折磨,而自己酿出的酒恰好能治愈躁狂症,于是走上了拯救人类帝国的道路。
47.5萬字8 7057 -
完結8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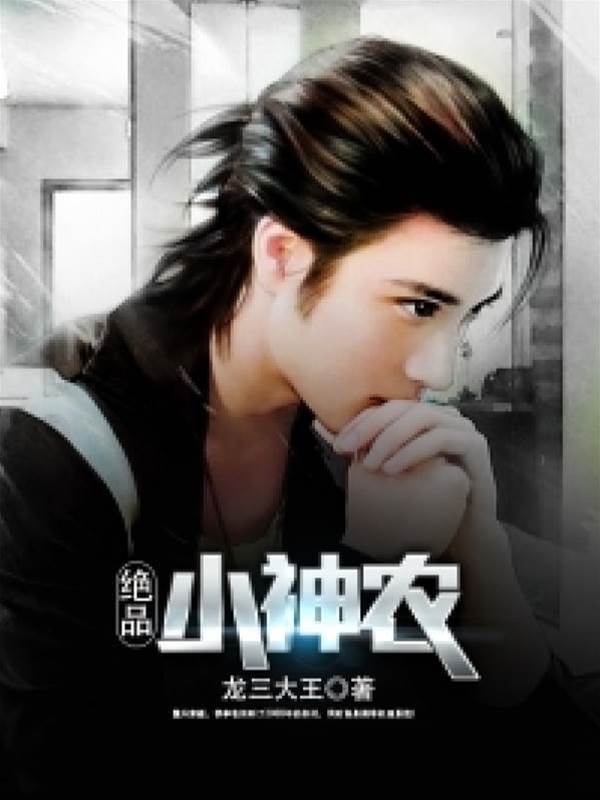
絕品小神農
意外穿越,使李牧回到了2008年的農村,同時自身攜帶征服系統! 武力,丹藥,法寶,蘋果18代,征服系統在手,要啥啥都有! 從此李牧開掛一般的人生,使農村成了世界的中心,同時村姑,村花,明星各種美女撲著喊著要和李牧回農村過‘幸’福生活!
186.7萬字8 36966 -
完結789 章

人生模擬器:開局忽悠老太監
楚塵一朝穿越到一個名為青州大陸的地方,而他所處的云月國,正值女帝當政,而他當下的處境正是要被割掉命根,好在系統及時出現,成功忽悠老太監,開啟假扮太監之路...
137.3萬字8 927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