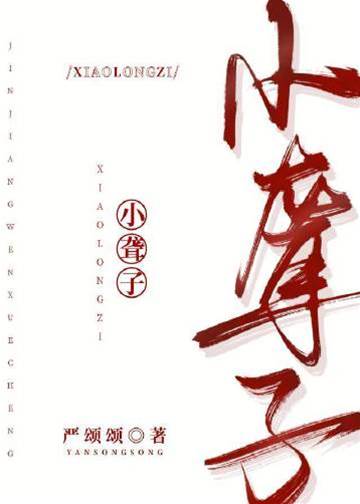《純良二代》 第19章
羅強閉了,沒再抬杠,深深地看著邵鈞。
再冷再的人,他終究不是一塊大石頭。
你要說他一點兒都沒,沒想法,那是騙人的。
邵鈞特自信,甚至帶著他與生俱來的自負:“咱有十五年的時間,慢慢來。我不信你就一直這樣兒,等到將來你出獄,我能讓你變一人。”
羅強在某個時刻有一種錯覺,自己一小孩兒了,眼前這人忒麼的,是老子的
“保姆”嗎?怎麼就把老子
“包”了呢……
羅強角了,似笑非笑,突然說:“給個煙。”
這是這個人服和解的表現。
只是,羅老二服了從來不會明說,老子認你了,咱倆別掐了。
邵鈞剛才還說沒煙呢,這會兒下意識地,讓那沙啞的聲音蠱著,從兜裡出煙盒,往自己裡順了一兒,再瞇眼一瞧,煙盒空了。
邵鈞又另個兜,把自己了一遍。
“沒了!……”邵鈞白眼兒一翻,氣呼呼的。
冷不防地,眼前白一閃,邵鈞沒提防,牙裡叼的那支煙就被走了!
羅強把煙塞自己裡,上下牙狠狠咬了幾口過濾,咬得全是牙印,這回想再易都沒人要了。
轉瞬間空氣裡的味道就不一樣,倆人仿佛又回到了那天午後盛滿的小病房,你一句,我一句……
羅強得意地咬著煙樂,樂出一口白牙:“火呢?”
邵鈞氣得真真兒的:“噯我說你這人!……”
邵鈞罵:“你這人要臉嗎?”
羅強逗:“你的臉我的臉?”
邵鈞一揮手:“滾,滾,排隊打飯去!去晚了沒了!”
羅強甩了一句,“我饅頭呢”,順手拿走了邵鈞擱在粥碗上的油餅,塞裡吃了,後是邵三爺一路窮追不舍的罵聲……
那些日子,邵鈞心裡還心著另外一個事兒。
國慶節眼瞅著沒幾天了,一盆盆金黃的花在大院裡擺出端莊的圖案。
市監獄管理局的領導國慶日那天要來清河參加升旗儀式,觀看隊列表演。
一大隊先前早就被選中參加表演,可是就在這當口,出了那兩檔炸號的事兒。
邵鈞考慮了很久,找到羅強:“誰,我想了想,你在新人班再待幾天,別調回七班。”
羅強挑眉問:“為啥不讓我回去?你想把我擱哪兒?”
邵鈞撓頭,現在不是把這人擱哪兒的問題,這人能在國慶隊列表演裡亮相?
邵鈞也煩領導沒事兒就跑清河溜一圈兒,好玩兒嗎?你們來溜達,我們還得集結訓練,列隊舉著彩球花球歡迎,一群頭大老爺們兒,傻不愣登地,你說你們這群領導搞這種勞民傷財的集面子工程,你們不累嗎?
你不累我們累啊。
可是煩歸煩,二九四這種人,萬一當天風了,在隊伍裡跟領導炸刺兒,把領導惹了,這可就把咱邵三爺的臉丟到全市了。
邵鈞問:“你真想回七班?”
羅強反問:“不然你把我塞哪兒合適?”
邵鈞心裡也明白,這二九四還只能去七班,因為只有七班的大鋪空了。
把這人塞三班,他一準兒跟老癩子掐起來;塞到五六八班,他早晚把五六八班的大鋪一個一個滅了。
這樣的人,你要管他,你要讓他服,只能先把他扶到他應該待的那個位置上。
每個牢號五個上下鋪位,靠門靠洗手間的位子是差位,無名小輩新犯人睡的。
而最靠裡靠窗那個床的上鋪,是每個班的班頭、大鋪。
那才是二九四應該睡的位置,邵鈞心裡清楚,其他隊長管教都清楚。
邵鈞歪頭問:“我能再信你一回嗎?”
羅強抬著下,角浮出想要耍賴的意味:“我饅頭吃膩歪了,我要是演好了,你給我發零食嗎?”
邵鈞上這麼說,心想就這號人二踢腳似的脾氣,我能信嗎?
你三爺爺要是再冒傻氣,就真了饅頭了。
他第二天下班,飛車趕回城裡,開得飛快,一大早兒直奔市公安局。
他敲開局裡檔案科一個人的辦公室,找對方幫忙。
邵鈞低帽簷,還一個勁兒解釋:“我爸不在吧?……沒有沒有,不在正好,我不找我爸,我就找你……麻煩你幫我查個人。”
那人一看,這誰啊?
這邵國鋼的兒子,立刻就擱下手裡活兒不幹了,幫他查。
公安局抓捕歸案的嫌疑人,建有部檔案,要碼的,只有部人士才查的到。
邵鈞平時從來不進這座大樓找他爸,也不樂意見人長輩,還得打招呼。
這次要不是為了查這個,他才懶得跑一趟呢。
他其實問過正主兒好幾次,二九四就是不說。
倆人跟較勁似的,你不是能查麼,你有本事查啊!
邵鈞在部資料裡檢索了一圈兒,把最近幾年的全查了,竟然有十幾個
“周建明”,最後終於找著那個強/犯。這人快五十歲了,媳婦跟人跑了,五年前在北京落網,判了十五年,押回當地監獄服刑,本就沒去過清河。
檔案科這人特熱心,想拍邵公子馬屁,問:“你要查的人啥名?你坐著,我幫你查,查到告訴你。”
邵鈞聳肩:“我也不知道啥,我就認他長相。”
“犯的什麼罪?”
“二九四。”
邵鈞突然問:“去年你們辦的涉黑□刑事案件,最大、最高級別的案子,都抓的哪幾個人?”
那人皺眉說:“你是要找那幫人?抓的最大的就三個……譚,李,羅,你查哪個?”
邵鈞定定地看著對方的眼,腦子裡過電影似的閃過那天在三裡屯高檔鴨店裡,服務生說過的話,“這幫孫子,都是讓咱羅總剩下的”。
邵鈞幾乎已經篤定了……
他手指甚至有些出汗,快速打出那個名字,按下
“確定”。
這回嘩啦一下搜出來五十幾個同名同姓,橫改革開放以來曆屆領導班子的大大小小各次嚴打。
邵鈞就好像腦頂上裝了一盞指路明燈,一下子就點開他要找的那一頁。
一張高正面清晰的新犯標準大頭照,忒悉的一雙濃重眉眼,目像帶鏽的釘子幾乎紮破屏幕。
羅強。
三十九歲。
戶口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區廠橋派出所。
二零零五年被公安機關依法逮捕。二零零六年以組織和領導黑社會罪、非法持槍罪、非法販賣運輸槍支彈藥罪、尋釁滋事罪、聚眾鬥毆罪、故意傷害罪、行賄罪、非法經營罪……等等數罪並罰,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16
16、正名...
第十六章正名
金秋十月,微藍如洗的天像一只亮的蛋殼,罩著城外荒郊這片純白的廠房。
監獄大鐵門上打出歡迎領導視察的條幅,廠區和生活區到懸掛著
“喜迎國慶謝政府恩社會”、
“認真學習努力改造重新做人”之類的大標語大橫幅……
那天,長駐清河監獄的全幾千名囚犯站在大場上,規規矩矩地排好隊,舉行升國旗唱國歌的儀式。
也是那天,一大隊作為三監區的標兵隊伍,在領導面前做了一場完整的隊列演練和軍表演。
邵鈞從來沒像那天似的,那麼張。臺上不就是司法部下屬監獄管理局幾個領導嗎,大部分人還沒有他爸爸大、級別高,更不如他姥爺當年——可是他真張。
他站在一大隊排頭,指揮隊列,他側後方一步遠的地方,站的就是羅強。
邵鈞那天一直七八糟有的沒的瞎琢磨,羅強這脾氣子,靠不住,羅強遲早要炸,這人能熬過升國旗唱國歌幾分鐘之後就得。
他腦海裡閃過無數種可能,羅強可能會在他要求全隊報數的時候扯開嗓門罵街,可能甩開步子一腳踢飛眼前的一盆花踢到主席臺上砸翻領導的茶杯,甚至可能在做的時候直接薅住他後某人的服領子一個過肩摔然後整個隊伍形式大打一團哭爹喊娘……
可是那天羅強特別安靜,特別認真。
邵鈞無數次眼角瞟過羅強的臉。羅強站在七班的排頭,喊口令的神特嚴肅,報數嗓門很大,吼得七班那一排小崽子一個個兒也張,脯得板直,一個數也沒喊差,一個步子也沒邁錯,齊步是齊步,正步是正步的,做的一招一式,特別規範賣力。
七班的崽子也是因為剛換上這位厲害的班頭,正於戰戰兢兢的適應期,都怕二九四怕著呢,誰敢不好好表現?
誰敢滋炸刺兒?
羅強跟班裡的人事先把話說在前頭:“大夥也知道了,從今往後,我是這個班的大鋪。你們以前看我順眼不順眼的,只要你在這個班待一天,你聽我的話,我負我的責。你樂意我一聲大哥,老子就樂意認你這個兄弟。”
“之前那些炸炸哄哄的爛事兒,過去了,我沒看見,我也不掛心。從今往後,大家是一個號的兄弟,別讓外班的人瞧咱們七班的人慫,不給勁兒,獎狀啊優秀啊都是別班的,背分啊炸號兒啊都咱們的?咱別讓人瞧不起。”
“這回國慶匯報演出,能不能演好!”羅強吼了一嗓子。
“能演好!!!!!”七班的崽子們一個個兒狠狠地點頭,繃得倍兒直,小肚子哆嗦著。
那天的國慶演出,一大隊表現出,最終在監區評比裡混了個優秀。
上邊兒視察得很滿意,下邊兒做工作的也松一口氣。監區長後來開總結會的時候還特意提了一句,“某些隊伍,某些班,平時經常小打小鬧,在班級管理上比較有‘個’,是吧?
猜你喜歡
-
完結118 章
穿成炮灰O後他們獻上了膝蓋
樓停意外地穿到一本狗血ABO文中,他的身份竟然是十八線廢材Omega。 作為一個稱職的炮灰,他的人設既可憐又醜陋,是個被全網群嘲的黑料藝人。 當合約在身,被迫參加了一檔成名已久的藝人重回舞臺選秀的綜藝節目時,觀眾怒了。 “醜拒。” “這節目不行了,廢物來湊數?” “他出來我就跳進度!” 樓停出場,一身修身西裝,肩寬臀窄,完美比例一出場就讓剛剛還在摩拳擦掌準備彈幕刷屏的黑子愣住了。 黑子:“這人誰?長得還挺好看???” 節目導師:“這身衣服有點眼熟。” 表演時,樓停當場乾脆利落地來了一個高亢婉轉的海豚音,隨後音樂驟變,節奏分明的rap伴著爆點十足的舞蹈,在一眾目瞪口呆中樓停穩穩而立,像是矜貴的公子,樓停謙虛地自我介紹:“大家好,我是樓停。” 導師:“??剛剛那是什麼?” 黑子:“世界有點迷幻,我要讓我媽媽帶我走去家門去看看。” 總決賽後,樓停溫暖一笑:“這次來是因為合約在身,我其實不太適合唱歌的。” 觀眾:“您放下手中第一獎杯再說這話可能有點信服力。” 等到一年後,樓停站在百樹獎的頒獎舞臺上,舉著影帝獎杯,身負幾場票房過十幾億的電影男主後。 黑轉粉的粉絲們才明白:“這他媽……還真的不是唱
41.8萬字8.18 10163 -
完結125 章

限定曖昧
祈言十九歲回到祈家,外界為他杜撰了八百種悲慘身世。 祈言免試進入聯盟top1的大學後,同父異母的弟弟告訴大家︰“雖然哥哥以前生活的地方教育條件不好,為了拿到入學資格,家里還捐了一棟樓,但我哥很愛學習!” 祈言上課不是遲到就是睡覺,弟弟為他辯解︰“哥哥不是故意的,哥哥只是基礎太差,聽不懂!” 祈言總是偏袒貼身保鏢,弟弟心痛表示︰“我哥雖然喜歡上了這種上不得臺面的人,爸媽會很生氣,但哥哥肯定只是一時間鬼迷心竅!” 知道真相的眾人一臉迷茫。 校長︰“捐了一棟樓?不不不,為了讓祈言來我們學校,我捧著邀請函等了三天三夜!” 教授︰“求祈言不要來教室!他來干什麼?聽我哪里講錯了嗎?這門課的教材就是祈言編的!” ———— 祈言為自己找了一個貼身保鏢,合約兩年。鑒于陸封寒處處符合自己心意,祈言不介意對他更好一點,再順手幫些小忙。 合約到期,關系結束,兩人分開。 一次宴會,有人看見陸封寒站在軍方大佬身邊,眾星捧月,肩章上綴著的銀星灼人視線。 “這位軍方最年輕的準將有點面
49.8萬字8 7852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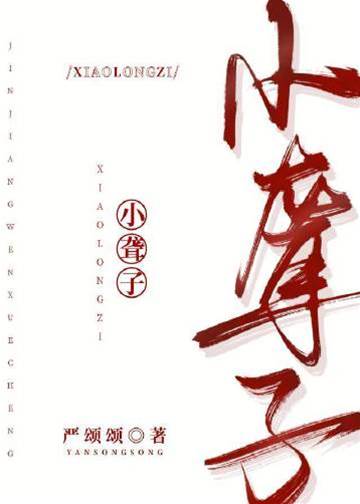
小聾子受決定擺爛任寵
憑一己之力把狗血虐文走成瑪麗蘇甜寵的霸總攻X聽不見就當沒發生活一天算一天小聾子受紀阮穿進一本古早狗血虐文里,成了和攻協議結婚被虐身虐心八百遍的小可憐受。他檢查了下自己——聽障,體弱多病,還無家可歸。很好,紀阮靠回病床,不舒服,躺會兒再說。一…
30萬字8.18 1761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