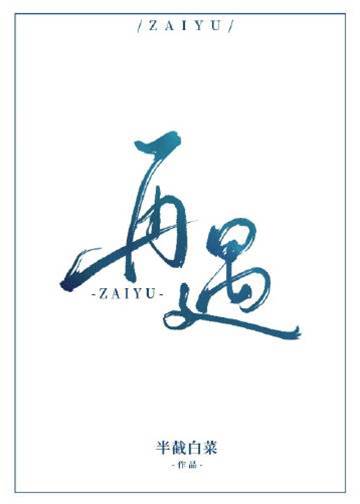《七零之改嫁前夫發小》 第 201 章(番外之我爬上前夫發小的床第章 第章 第章 )
陸殿卿陪著在廬山玩了三天,四都轉了,電影自然也看了,可以說非常盡興了。
干休所的飯也很好吃,可以隨便點,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林舒吃得特別心滿意足。
這天吃過飯,林舒懶散地躺在床上,隨口問陸殿卿:“服干了嗎?”
這邊的服很不容易干,洗了后晾在外面,晾半天一竟然滴水,霧氣太大了。
前天陸殿卿讓孫助理下山買了一些服送上來。
陸殿卿坐在旁邊,正低頭拿著地圖研究,聽到這個隨口道:“干了。”
林舒便湊過來:“你看什麼呢?”
陸殿卿便指著地圖說:“我們下了山后,可以坐漢九班船過江,這樣可以看看江上風景。”
林舒便有興致了:“好,我要坐船,我還要吃長江魚!”
喜歡這種覺,好像陸殿卿是那個日本畫片里的阿蒙,喊一聲,他就能變出來,什麼愿都可以滿足。
陸殿卿便陪著一起躺在床上,他靠著床頭,繼續翻著地圖:“你如果喜歡,我們可以去黃石玩,那里號稱半城山半城湖。”
林舒:“剛看了廬山,再去看這些也沒什麼意思了,我只想坐船吃魚。”
陸殿卿想了想:“那也行,我們先坐船,等坐了船,你看看想去哪兒,到時候再定。”
林舒打個滾,直接趴在他膛上,把玩著他的袖扣:“你哪來那麼多時間?你不忙嗎?你們單位也不給你打電話?”
陸殿卿很不在意地道:“打什麼電話,這里手持電話都沒信號了,他們怎麼可能找到我。”
林舒驚訝,仰臉看他:“太不負責任了,說都不說一聲人就消失了!”
這是他說過的,現在原封不地還給他了。
林舒有些得意,故意道:“難道不是嗎?天底下像你這麼負責任的人也不多了!”
他眸間泛起笑,手指溫地幫順了順頭發:“地球離了我又不是不會轉了,再說那只是工作。”
林舒攬住他的頸子撒:“是不是可以一直拋下工作陪我?”
陸殿卿不答反問:“你需要我一直陪著你嗎?”
林舒輕哼:“你最擅長的,是不是就是把問題拋給對方?”
陸殿卿:“你不愿意回答我,卻要我回答你?”
林舒便笑著道:“好,那如果我說,我希你拋下一切,一直陪著我呢,什麼都不用管,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陸殿卿注視著:“好,我可以拋下一切,一直陪著你,什麼都不用管,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林舒側著臉,將臉頰在他膛上。
結實的膛理清晰,屬于男的清冽氣息將淹沒。
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傍晚太從窗戶里照進來,炫白的一片。
喃喃地說:“我知道你在騙我,不過沒關系,我喜歡聽。”
果然人都是喜歡甜言語的,哪怕是假的,當時聽著開心,那就很好了。
陸殿卿垂眸凝視著的發:“我也知道,你在騙我,你并不需要我一直陪著你,是不是?”
林舒:“你看,我們都在騙對方。可是即使這樣,我還是很,我愿意被你騙。”
陸殿卿聽這話,眸中泛起異樣的愫,他抿了抿,問:“你會騙我多久?很短時間?很長時間?”
林舒搖頭:“不知道,也許幾天,也許一輩子。”
陸殿卿便俯首下去,吻上了的發:“如果能騙我一輩子,我愿意被你騙,永遠不要醒來。”
林舒看著窗外那片太,有些累了,看得有些失神。
喃喃地說:“那天晚上,我為什麼下定決心導演了那一場鬧劇,你知道嗎?”
陸殿卿:“你說過,因為我下車后一直看著你,走到你面前,對你出手。”
林舒低聲道:“對,你喝醉了,你走到我面前,就那麼看著我,你的眼睛就像最的酒,讓人沉醉,你還對我出手,那一刻我不自,就想投到你的懷中。”
林舒了子,悶聲問:“陸殿卿,以前你是不是喜歡我?“
林舒:“那我以前為什麼沒有嫁給你?”
陸殿卿抬頭,過窗戶,怔怔地看著遠:“可能我不夠好,也可能我們沒有緣分。”
林舒也就閉上了眼睛:“當時我如果嫁給你,現在是不是過得很幸福?”
之后,兩個人都沒再說話了,房間很安靜,偶爾一陣山風吹來,帶來一陣甜香,似果香,又仿佛山澗泉水的清香。
林舒一直沒有,陸殿卿以為已經睡著了,他的手攬著的腰,低頭想著心事。
可就在這個時候,突然長長地嘆了一聲,之后道:“當年我如果嫁給你,我們現在應該在做什麼?會不會你帶著別的人來廬山玩?或者我陪著別的男人來廬山玩?”
林舒繼續暢想這個問題:“我現在給雷正德戴了一頂綠帽子,那我嫁給你,會不會給你戴綠帽子……不過我覺得我之所以給他戴綠帽子,是因為他先那麼對我,他不活該嗎?”
“我嫁給你的話,你對我忠心耿耿,我對你自然沒有二心,你說是不是?”
還想繼續琢磨,和自己夢想中的事較真,誰知道這時候陸殿卿卻一個有力的翻,將在
陸殿卿眉頭鎖,就那麼盯著。
林舒:“你干嘛……”
陸殿卿低頭,毫不猶豫地傾咬的。
林舒被咬得疼了,眼淚差點掉下來,委屈死了:“陸殿卿你是狗嗎?”
陸殿卿淡淡地道:“我就想當狗,怎麼了?”
林舒不可思議:“這怕不是有病!”
陸殿卿面無表:“既然當了狗,當我就要當個盡興。”
林舒無言以對:“你!”
他確實很不要臉,仿佛有病,而接下來,他甚至開始毫無恥地做了一些毫無恥的事。
林舒就算結婚多年,也沒這樣過。
有些接不了,哭著胳膊去推他腦袋:“陸殿卿,你真不要臉,你放開,求求你放開,不能這樣!”
陸殿卿也不管,就那麼小口地含著,咬著。
門外雖然沒靜,但是林舒知道,保鏢岳青一直在無聲地走。
也許人家什麼都聽到了。
林舒恥地咬著,含著淚說:“外面肯定聽到了。”
陸殿卿終于抬起頭,眸晦暗,上瀲滟,他盯著含淚的眼睛:“沒什麼,他守口如瓶。”
岳青是過專業訓練經驗富的保鏢,是他三叔知道他差點出事后特意為他安排的。
林舒惱至極,便用牙齒咬他肩膀:“你以為我是怕他說出去嗎?”
是讓人聽到靜,就很恥了。
以前哪里知道,那個一臉正人君子的陸殿卿這麼不要臉?
越想越覺得,那天晚上自己失算了,為什麼以為自己可以算計他,分明是自己被他算計!
陸殿卿撐著胳膊在上方,深邃的眸子就那麼盯著看,臉上泛著紅暈,仿佛白瓷鍍上一層人的釉,這是他為染上的彩。
這讓他越發沉迷,就像發現了新大陸,會忍不住想一口將吞下,想繼續挖掘,探索。
他甚至覺得自己前面三十多年白活了。
他就這麼盯著道:“我發現不回去好的。”
林舒:“為什麼?”
陸殿卿啞聲道:“在這里沒人認識我們,我們可以隨心所,放浪形骸,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我現在已經不太認識我自己了。”
林舒哼了聲:“我也快要不認識你了,我懷疑你是假的陸殿卿!”
陸殿卿想了想:“可能以前的陸殿卿才是假的,誰知道呢。”
林舒聽著,想起以前的他。
年時,他沉默認真,坐在庭院中練書法,一筆一劃是那麼一不茍,其實那時候林舒會忍不住有個壞念頭,推他一下,讓他把那幅字寫一個七八糟。
青年時,他嚴謹斂,有著舊日世家公子的疏淡冷漠,便是事待如何得,也讓覺得,那不過是一種不聲的高高在上罷了。
到了這時候,他已經功名就,云淡風輕的一個抬眼,便已讓人心生畏懼,卻仿佛過著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沒有人,沒有音樂,守著不知道多年的老房子,喝著寡淡無味的白開水,墻上再掛一幅陳年字畫。
忍不住笑起來,手了他線條分明的下頜線,很有些調戲地道:“那你得謝我,是我把你引正道。”
陸殿卿眸深邃,邊含笑:“正道?你好意思說出口嗎?”
林舒很不要臉地道:“怎麼,你不喜歡?”
陸殿卿指尖了的臉頰:“喜歡。”
他想起以前,眸中泛起了回憶:“我在想,如果是現在的我,回到過去,我會做什麼?”
林舒頓時興致□□來:“會怎麼樣?”
陸殿卿垂眸看著發亮的眼睛,卻不說話了。
林舒不干了,撒:“快說!不然不和你玩了!”
陸殿卿翻,側躺在旁邊,才低聲道:“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去王府井書店,順便去百貨商店取一樣東西,恰好遇到你和他。”
陸殿卿口中的“他”自然指的雷正德,他已經不太愿意提及這個名字了。
林舒聽得津津有味:“然后呢?”
陸殿卿:“到你們好像在選一塊布料,可能是做服吧我也不太清楚,當時你想選一個,他覺得另一個好,你們為了這個差點吵架,你不高興了,他就哄你,說聽你的,你便笑起來,你笑得很開心的樣子。”
林舒一下子沉默了,這應該是結婚前的事了吧,但是不太記得了。
和雷正德相中有太多爭吵,大部分時候他還是比較讓著的,總是能占上風,不過也正是因為這個,才被哄住了,反而在雷正德父母面前比較恭敬,以為那是自己的本分,又覺得在雷正德那里找補了。
不過最后,也是雷正德給了狠狠的一刀,直心窩子的一刀。
陸殿卿淺淡的眸中有些恍惚:“我在想,如果現在的我,回到當初,我會怎麼辦?”
林舒側首看著他,好奇:“會怎麼辦?”
陸殿卿:“我會走上去,握住你的手,告訴你不要和他結婚了,嫁給我吧,我全都給你買,各樣來一個,不行我們把店搬回家,然后當著他的面,抱著你吻。”
林舒安靜地看著他:“然后呢?”
陸殿卿的視線落在臉上:“把你搶過來,你是我的,和他沒有關系。”
林舒:“如果那時候的我不愿意呢?”
陸殿卿淡聲道:“不愿意也沒關系,反正你是我的了,先搶了再說。”
林舒一下子笑了,回想了當時自己的種種心思,終于道:“我從云南回來后,你就不理我了,我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你了,其實有一段我難過的,不過后來我就不當回事了,我心想,和我沒關系,我才不會在意你,那個自以為是的人。”
陸殿卿抬起胳膊,將攬在懷中:“是我不好。”
現在說這些,也只是說說罷了。他明白,哪怕再來一萬次,當年的他也是當年的他,并不能做出今天的種種。
那時候,他家中境況剛剛從政治抑中走出來,他自己又是在老一輩的教育中啟蒙,在十年抑中長大的,那個時候也還沒改革開放,沒有接外來文化的沖擊,大家不懂什麼是,大家也不懂什麼是追求。
他在那保守苦悶之中,只知道默默地惦記著自己心的孩,卻不會訴諸于口。
林舒卻在這時,吻了吻他的線:“如果當年,你真敢走上去吻我,我一定跟著你走。”
陸殿卿眸中深暗滾燙,盯著道:“是嗎,你覺得回到當年,我好還是他好?”
林舒挑眉笑道:“說這話有意思嗎?”
陸殿卿:“嗯?”
林舒:“你為什麼要自降價,和一個沒種的男人比?他配嗎?”
陸殿卿默了下,之后笑出來,便抱著低頭親。
兩個人這麼鬧了一場,都鬧了一個氣息不穩,林舒才想起一件事:“你找我的事,別人知道嗎?會不會傳出去?”
陸殿卿低頭端詳著:“你希我怎麼理?”
林舒想了想:“我就擔心你鬧大了,傳出去,這樣對大家都沒好。”
一旦和陸殿卿的事傳出去,雷家必然抓住自己的把柄,那自己便于弱勢。而從陸家方面,當然明白,陸殿卿攪自己和雷家之中,還為一個不彩的角,對他的聲名,對他家中長輩的大事,都是極大的丑聞,甚至可能被人利用,影響到更大的層面。
陸殿卿:“好,我明白了,我會理好。”
林舒:“可是你找人,又跑出來,這事能瞞過去嗎,你家里人會不會知道了?”
陸殿卿安道:“沒什麼,這些年我在外面做事,和家里其實瓜葛不大了,我做的許多事他們也不清楚。這次找人也是用了四九城外的關系,如果說瞞不住,那也只有我三叔瞞不住,不過我三叔一向講義氣,和我也談得來,我回頭讓他幫我掩飾下就是了。”
林舒聽著,記起來,他三叔是軍方的,看來這次他找人,應該是用了他三叔有瓜葛的關系。
松了口氣:“那就好,萬一你家里知道,把你劈了怎麼辦?”
陸殿卿聽著,無奈看一眼:“至于嗎,我都這麼大了,還不至于被人這樣管著。”
下了廬山后,陸殿卿的手持電話有了信號,孫助理接了一個又一個電話,其中有一個重要會議在上海,面有難地試探陸殿卿意思。
陸殿卿直接說不去了:“說了讓你關機,不要接電話,你接了電話自己回復吧。”
孫助理愁眉苦臉,不過沒敢說什麼,小心地回電話去了。
一行人做的是漢九班客,現在不是什麼高峰期,陸殿卿直接包下一艘客,讓那客隨便開,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不得不說,有錢的覺真好。
一聲高悠揚的汽笛之后,客啟航了,林舒便微靠著陸殿卿,和他說話,偶爾逗逗他。
反正客上沒外人,就很隨意,毫不忌憚。
覺得循規蹈矩不好,當壞人才好,在陸殿卿邊當壞人的覺尤其好,很有種興風作浪敗壞朝綱的覺。
反正陸殿卿寵著,說什麼就是什麼。
至于邊的保鏢陸青和孫助理,管他們怎麼想呢!
猜你喜歡
-
完結72 章

心機女的春天
韓熙靠著一張得天獨厚的漂亮臉蛋,追求者從沒斷過。 她一邊對周圍的示好反應平淡,一邊在寡淡垂眸間細心挑選下一個相處對象。 精挑細選,選中了紀延聲。 —— 韓熙將懷孕報告單遞到駕駛座,意料之中見到紀延聲臉色驟變。她聽見他用浸滿冰渣的聲音問她:“你設計我?” 她答非所問:“你是孩子父親。” 紀延聲盯著她的側臉,半晌,嗤笑一聲。 “……你別后悔。” 靠著一紙懷孕報告單,韓熙如愿以償嫁給了紀延聲。 男人道一句:紀公子艷福不淺。 女人道一句:心機女臭不要臉。 可進了婚姻這座墳墓,里面究竟是酸是甜,外人又如何知曉呢?不過是冷暖自知罷了。 食用指南: 1.先婚后愛,本質甜文。 2.潔黨勿入! 3.女主有心機,但不是金手指大開的心機。
22.8萬字8 6676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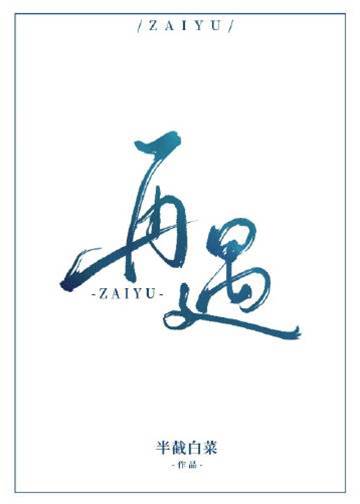
再遇
孟淺淺決定復讀,究竟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應浩。她也不知道。但是她成功考上了應浩所在的大學。一入學便得知,金融系應浩正跟金融系的系花談戀愛。-周喬曾說應浩不是良人,他花心,不會給她承諾以及未來。孟淺淺其實明白的,只是不愿意承認,如今親眼所見,所…
38.8萬字8 17711 -
完結413 章

染指
昏黃光影下,葉蘇芙直勾勾地盯著男人瞧。 瞧他肌肉勃發,肩寬腰窄。 夠勁! 江清野嫌她貌美,愛勾人,不老實。 后來他食髓知味,身心俱陷。 橫批:真香! (美艷釣系富家千金X又粗又野糙漢)
50.6萬字8 7272 -
完結78 章

杳杳歸霽
蘇稚杳是眾星捧月的人間嬌氣花,清高,貌美,從頭髮絲精緻到腳後跟。賀氏掌權人賀司嶼冷峻迷人,混不吝到目空一切,所有人見了他都得躲。兩位祖宗井水不犯河水。直到某天,蘇稚杳因得罪賀司嶼被架走,下場慘烈。蘇父琢磨,吃點苦頭長記性,甚好。 後媽假惺惺唱白臉,繼姐更是幸災樂禍……殊不知當晚,賀家別墅。男人咬著煙,慵懶倚在沙發,襯衫被埋在身前的女孩子哭濕了大片。“他們果然都是虛情假意,一天了都沒來救我,嗚嗚嗚……假的都是假的……”
39.3萬字8.57 63175 -
連載113 章

顧總天臺涼不涼,方小姐她另尋新歡了
外人說顧行之光風霽月,運籌帷幄。隻有他自己知道,方梨是他命裏最大的變數。……後來,方梨轉身離開,再無音訊。顧行之紅著眼站上天臺:“她真的不會回來了嗎?”再後來,顧行之一把抱住方梨,“你真的不要我了嗎?我可以和孩子姓。”
20.9萬字8.18 71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