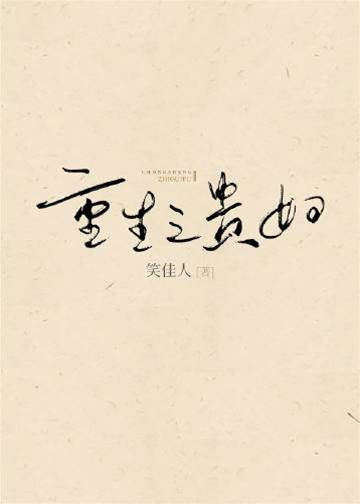《姑母撩人》 第51章 第51章
說話間,聽見窗戶上“篤篤”敲了兩聲,外頭立著抹纖影。花綢過去,過茜紗瞧見是紅藕,立時迸出個笑來,“你瞧外頭窗戶也上了鎖,打不開的,你只把東西從窗里塞進來。”
“噯,”紅藕應著,將一個信封塞進來,一頭囑咐,“桓哥兒說不可多了,只怕得你不住。”
“就他蝎蝎螫螫的,不妨事。”
花綢接了東西,追回去,拿了信封到床上打開來瞧,里頭卻是短短兩截枝,上頭結了好幾片葉。
椿娘挨著看一看,心下好奇,就要手去枝椏,被花綢狠拍一下,“這個山漆,上人上就要起紅疹子,死個人呢!京城里不常見,也不知桓兒哪里弄來,你且別,先收起來,等午間送飯的丫頭過來,我先裝出發熱的樣子,你好他們告訴太太請大夫,大夫來前,我就抹在上,必起疹子。”
兩個人小心折起信封,塞在枕頭地下,靜待太懸空,樹蔭移窗,丫鬟提著食盒送來飯。
進屋擺了飯,卻久不見花綢出來,便向椿娘調笑,“這個時候還沒起?”
椿娘裝得好模樣,坐在案前風僝雨僽,“姑娘昨兒夜里上有些燒,到晨起就說上不爽快,我喊起來坐了一會兒,又沒神,又睡了過去。”
“喲,”那丫頭走到門簾子前,開條往里瞧,果然見花綢還睡在帳中。又走回來,在案上坐著與椿娘說話,“這時節,將熱未熱的,大約是夜里掀被染了風,可燒了滾滾的茶來吃了?”
“一早起來就吃了四五盅了,我想也是傷風,便蓋了兩床被在上,又總嚷嚷熱,死活不蓋。姐姐,你去回太太一聲,是請個大夫來瞧瞧還是怎麼的?”
“自然要回的。”
那丫頭轉走到魏夫人房中,將這一節提起。魏夫人冷端起腰,拈帕子撣撣面,“這個媳婦兒,專會裝怪,關這些天,口里死活不肯認錯,卻把自己做起病氣來嚇我。我是嚇大的呀?要死就憑去死好了,我煜晗好好的人品,如今又升到太常寺卿,就再續一房千金小姐也續得!嘛,就病著好了,不許請大夫瞧!”
巧在那單煜晗為著奚甯那一檔子事,近日忙著與潘商量主意,不得空過問家中事,便耽誤了兩日。花綢見不請大夫,裝得愈發嚴重起來,連著兩日不吃飯,送飯丫頭瞧了,只好走到魏夫人房中勸:
“瞧那樣子,像是真病了,太太還是請大夫來瞧的好,倘或有個好歹,奚家來問,咱們如何開?看好了,諒病這一場,往后也肯乖乖聽話了。”
那魏夫人細細思來,便請了家中長請的大夫來。那大夫雖是單家常請的,可在來前,早被奚桓暗中威了一番,又許了他幾百兩銀子,這倒是在單家瞧幾年病也攢不下的錢,大夫無有不應。
這廂背著醫箱子走到單家來,隨著人進屋,先隔著帳子把脈,稍刻便把一對稀稀拉拉的眉掉了幾,“能否揭帳讓小的觀觀夫人病容?”
幾個丫頭面面相覷,椿娘索大大方方開帳,“大夫請觀。”
那大夫觀一觀星眼,又觀觀病額,又吐出一截舌來瞧瞧,裝模作樣窺一番,把眉越越,俄延半晌,口里嘟囔著“得罪得罪”,手上卷起花綢的袖口來。
眾丫頭跟著歪腦袋一瞧,見花綢手臂上好些紅疙瘩,不由驚呼,“這是什麼病?”
不問便罷,一問,那大夫先跳開幾步遠,急得腦門上發汗,“不好,是痘瘡①!”
“痘瘡?!”
這病向來令人聞風喪膽,患者發熱頭疼,上起痘疹,極容易過人,得了此病,九死一生。丫頭們雖沒見過,卻都聽說過,眼下一見,紛紛避走外間,唬得渾冒汗,你窺我我窺你一陣,竟都丟下花綢去回稟魏夫人。
那魏夫人聽見,當下有些膽,使人請了大夫來,卻不許人近,隔得八丈遠問話,“大夫,這病實在沒法子?”
大夫搖首嗟嘆,“雖有些藥方,卻多是拖延之,得了這個病,有見好的,別說病人,就是跟前伺候的,只怕也不好。夫人切勿往病患屋里去,也不要許跟前的人去,只/床前侍奉的人每日煎了藥給病人喂服,好不好,還看造化吧。”
魏夫人心有余悸,一只手撳在心口,扶椅坐下,半天木呆呆不講話,直到那大夫寫下藥方,囑咐幾句,走了半晌,才回過魂兒來。斜眼一瞧,那幾個方才進屋去瞧的丫頭早哭得雨打梨花一般,都生怕染上了病。
屋里嗚嗚咽咽哭得魏夫人三魂丟了七魄,著使人去報老侯爺,拿方子抓藥。
鬧足一陣,聽見單煜晗歸家來,忙使人將他到跟前來囑咐,“媳婦得了痘瘡,你回去使丫頭將先前用過的東西都燒了,你也換一間屋子睡,千萬別去瞧,可記住了?”
單煜晗屁還沒坐定,冷不丁聽見這消息,臉大變,“好好的,怎麼會得痘瘡?”
“這家里并沒有個源……”魏夫人絞著絹子細想,一顆心還惴惴不定,“不得是去碧喬胡同染上的,只是現如今才病發出來。碧喬胡同是什麼地方,三教九流什麼沒有?你父親的意思,還將現住那間屋子鎖起來,單使的丫頭侍奉,若好了是造化,若不好,早早抬出去,免得帶累全家的命。”
緘默半晌,單煜晗悵然地點點下,“也只好如此了,母親做主吧。”
言訖拜禮出去,玉樹珊珊的側影一幀幀過長廊,斜熨帖在他的側臉,是金燦燦的冷漠與無。
闔家哄哄憂愁難計之際,卻有月懸螭吻,銀河星好。影橫在窗上,被燭暈染得格外迷人。
更迷人的,是潺湲的夜風,從未如此帶著無限的希朝花綢吹來,要不了兩天,就能回家了,思及此,竊竊的笑聲似春風弄笛,鶯蹄林間。
“哎喲!”正笑如風拂菡萏呢,冷不防手臂上又犯一陣錐心的。
忍不住要去撓,虧得椿娘外間端藥進來,忙喝住,“快別撓!仔細撓破了留疤。”說著,將藥擱在炕桌上,下朝花綢抬一抬,“姑娘,這藥怎麼好?”
“傻子,擱涼了倒在花盆里就是。”花綢疊歪腰倚在榻枕上,拿把扇不住往手臂上扇,稍稍止了,“噯,紅藕方才來送藥時可說什麼了?”
椿娘止不住笑得花枝,挨著奪了扇替打,“說是滿府里急得要不得,方才屋里跟著瞧那幾個丫頭,哭得沒法子,生怕染了病,連太太也不許們出屋子走了。太太險些嚇破了膽,不許人往這里來,就連藥也是到那邊屋里給紅藕,再使紅藕送過來,瞧這樣子,都怕被咱們給帶累病了。”
“虧得那大夫,是個守誠信的人,收了桓兒的銀子,倒也不怯,說得有模有樣的。”花綢朱巧囀,一副輕松神。
“也是姑娘裝得像,”椿娘豎起個大拇指,連連稱贊,“憋得那一臉的汗,眼也半睜不睜的,真像個將死之人。”
“呸,你才要死。”花綢笑一笑,漸漸又愁上眉心,“就怕娘聽見,將嚇出個好歹來。”
“姑娘放心,桓哥兒既出了這法子,自然也有法子哄太太。只是不知他幾時來,我想,他明日來才好。”
花綢皺著鼻子狠剜一眼,“你又想他來了?你從前總我遠著他,這會子又盼他,心也轉得忒快了些。”
“嗨,誰知道單煜晗是這樣的人,我是時時都為姑娘想的,從前勸姑娘遠著他,也是為您好,如今不勸,也是為您好。跟單煜晗這樣的豺狼過一輩子,才真是害了姑娘,若有法子,永遠離了他才是,只是就算姑娘擔得起流言蜚語,我看他也斷不肯輕易就放了姑娘。”
“走一步看一步吧,車到山前必有路。”
花綢笑嘆著,將腦袋依在窗畔,斜眼見明月漸滿,像一個玉盤,從生出勇氣的那天起,便日益盛著盈的希,一日多過一日,終有一日,這些問題都不再能為困擾的問題,會闖過這些牽制,朝的人與日子靠近,連這間悶屋子也為流溢著歡喜。
到下一日,花綢得了痘瘡的消息便走到奚府,奚緞云剛一聽見,險些嚇暈過去,扶住榻寸寸跌坐回去,好像天榻了一般,得不過來氣,只覺心口絞痛得直不起腰來,不過須臾,眼淚就大顆大顆地砸在上。
可把奚桓嚇得一跳,忙上前攙扶,慌著手腳倒茶與,“姑別著急,我正要套了車往單家去,接了姑媽回家,咱們請宮里的太醫重新瞧過。他單家不過是請的外頭的野郎中來瞧,多半是診錯了,我那日見著姑媽還是好好的,哪里會得這種病?您千萬安心,等我去接了人來再說。”
奚緞云黑漆漆的眼前像是驀地迸出點,急攥住他的腕子,“真的?我要嚇死了,好孩子,你快去接回家來,只怕單家聽見是這個病,避還避不急,哪里會悉心照料?!”
“正是這個意思,您先別顧著哭,我這就去!”
奚桓又急又怕,急著去接花綢,怕則怕將奚緞云嚇出個好歹來他如何擔待?于是忙著招呼人套車,帶著七八個人小廝往單家去。
紅日風搖翠柳,八分春去,一半杏花休,卻道是,云山重疊,分釵合鈿,歸期在眼前。這廂坐在馬車里,想著接花綢回家,只把春風笑斷,笑得虎牙歪出,著一天真的孩子氣。
卻在單府門前,收斂了天真,只表出不聲的沉穩。走到廳上,見單家二老皆在,他拂整袍上前恭敬作揖,“二老一向子康健?”
“好、好,”老侯爺忙將拐杖抬一抬,向他指坐,“聽說小公子殿試得了探花?真是年有為,奚大人養了個好兒子啊,日后你父子二人同朝為,確是朝廷之福,天下之福啊。”
奚桓謙卑言謝,將魏夫人脧一眼,眼神凜然間迸出些冷意,“我今日來,是家中長輩之命,前來探姑媽。聽說姑媽染重疾,家父與姑十分擔憂,不知得的是什麼病,二老怎麼一早不使人到家報個信兒?”
這一問,頗有些興師問罪的意思。那魏夫人在上首,把下頜稍稍低垂,訕訕發笑,“大夫說是痘瘡,我們家里并無一人得過這種病,也不知是哪里染來,急得闔家作一團,我與老爺煜晗一夜沒合眼。”
震懾兩句后,奚桓又言相笑,“姑媽一向孱弱,從前在家就三朝五夕的生病。家父的意思,若是別的病,倒罷了,只是這個病不可掉以輕心,想著將姑媽暫且接回家治療。一則,我家園子大,好將病人隔開,若在府上,只怕人來人往傳出去,帶累了二老與姑父;二則,我家一向是請宮里的太醫瞧病,就是南京醫署里也有相的太醫,或可請這些醫高明之人前來治療;三則,姑老人家聽見兒病了,急得險些暈厥,將兒接到邊,眼看著,終歸放心些。”
可巧那魏夫人正日夜懸心這個病過人,又怕奚家怪罪沒照顧好媳婦。眼前聽他一說,正中了的懷,喜得險些要笑出聲,到底忍者,拼命出兩滴眼淚拿帕子窮蘸著,“是我家的媳婦,原該是我家照料,別說是這個病,就是司里來拿人,我們也要與鬼差拼一拼的!只是你既如此說,一來接回去是為媳婦的病好,二來也是為親家母安心,我們自然沒什麼好說的。”
話音甫落,又忙慌慌添補幾句,“只是接回去,到底怎麼樣,好歹時時使人往家來遞信,我們曉得也好放心,結果好不好,我們都是要去接的,終歸是我們單家的媳婦,我們沒有不認的道理。”
“這是自然。”奚桓拔座起來,拱手作揖,“請帶我先去瞧瞧。”
那魏夫人要帶他去,又怕過上病,便來丫頭領著往那屋里去。這時節花綢正睡在床上裝病,聽見聲音,著急忙慌翻起來在窗戶上瞧,見一個魂牽夢縈的影迤行而來,喜得一顆心隨他的步子咚咚跳個不停,險些從口里跳出來。
椿娘跟著一瞧,忙將拽回床上,“快躺著,別這節骨眼兒上人瞧出來了!”
說話牽了被子將渾裹住,出一張蒼白的小臉,眼兒將開未開,淡將啟未啟,眼瞧著簾外來人,被子里抬起只滿是紅疙瘩的小臂朝他過去,“桓兒,你來了?”
這弱弱的一聲喊,險些把奚桓的心喊停了,又見釵橫髻亸,臉慘白,眉間凝恨,游一系,他一時也恍惚起來,紛擾擾分不清真假,只顧去抓的手,“姑媽,您好不好?”
花綢瞧他急了,忙趁丫頭不注意的間隙里朝他眼,他這才心里落停下來。這廂使椿娘揀了裳,又等著紅藕收拾了些要東西,拿了件斗篷將花綢團團裹住,勾著彎便抱起來。
走到外頭,魏夫人見抱著甚為不妥,又想人家是自教養長大的侄兒,與兒子無一般,不好說什麼,只是隔得八丈遠地假意囑咐幾句。
不巧在府門口撞見單煜晗衙門歸家,正打馬車上下來,瞧見烏泱泱一堆人,又瞧見是奚家的車馬,心知是來接花綢回去養病。
正有些疑,倏見奚桓抱著花綢出來,心里有些不悅,面上卻周道著,“瞧見門前的馬車,我就猜準是世侄來了,聽說殿試點了探花?我一時有些忙,還沒上家中賀過,請勿怪罪。”
奚桓把步子放慢,從石磴上蹣步下來,著他笑,卻有些高高在上的疏遠,“小小探花,不敢勞駕大人。”
花綢窩在他懷里聽見單煜晗的聲音,只怕橫生枝節,麼將奚桓的裳掣一掣,示意他趕走。
奚桓卻不急,刻意抱著走向單煜晗,“大人向來公務纏,連我姑媽病重,也不見在家守護,可見大人為公之心尚能拋家舍業,我又怎麼敢勞大人尊駕來賀?”
見他角噙笑,眼凜然,單煜晗猜出他心有不善。又看花綢病懨懨窩在他懷里,似落子歸棋,春燕歸巢,驀地他心里不痛快。
可又怕過了病,不得不將腳退了幾步,“世侄如今大了,還與姑媽親如母子,我瞧見亦不容。只是大路上,這樣抱著終究不好看,放下來丫頭攙扶著就是。”
“噢?”奚桓乜眼一笑,兩手將花綢微微遞給他,“姑媽病重,有些走不得,你們是夫妻,不如大人抱上車?”
行間,花綢的手垂下來,出半截紅疹滿布的手臂,單煜晗瞧見,眉宇驚蹙,不聲地又連退了兩步,白白對花綢囑咐兩句,“你回到岳母邊養病,我也放心,等過兩日我得空了去瞧你,千萬珍重。”
奚桓笑一笑,“那我們先告辭。”那目,仿佛是端坐在天上的神明不經意瞥見人間的螻蟻,連不屑都懶得。
單煜晗側臉瞧著他不可一世的背影,肚子里像有新的一場大火燃起,將他一雙目燒得寂若死灰。
————————
①痘瘡:天花。
猜你喜歡
-
完結181 章
鳳隱天下
洞房夜,新婚夫君一杯合巹毒酒將她放倒,一封休書讓她成為棄婦!為了保住那個才色雙絕的女子,她被拋棄被利用!可馳騁沙場多年的銀麵修羅,卻不是個任人擺布的柔弱女子。麵對一場場迫害,她劫刑場、隱身份、謀戰場、巧入宮,踩著刀尖在各種勢力間周旋。飄搖江山,亂世棋局,且看她在這一盤亂局中,如何紅顏一怒,權傾天下!
17.9萬字8 43522 -
完結418 章
鳳逆九天:一品毒妃傾天下
她是將軍府的嫡女,一無是處,臭名昭著,還囂張跋扈。被陷害落水後人人拍手稱快,在淹死之際,卻巧遇現代毒醫魂穿而來的她。僥倖不死後是驚艷的蛻變!什麼渣姨娘、渣庶妹、渣未婚夫,誰敢動她半分?她必三倍奉還。仇家惹上門想玩暗殺?一根繡花針讓對方有臉出世,沒臉活!鄰國最惡名昭著的鬼麵太子,傳聞他其醜無比,暴虐無能,終日以麵具示人,然他卻護她周全,授她功法,想方設法與她接近。她忍無可忍要他滾蛋,他卻撇撇唇,道:“不如你我二人雙臭合璧,你看如何?”【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109.7萬字8 73405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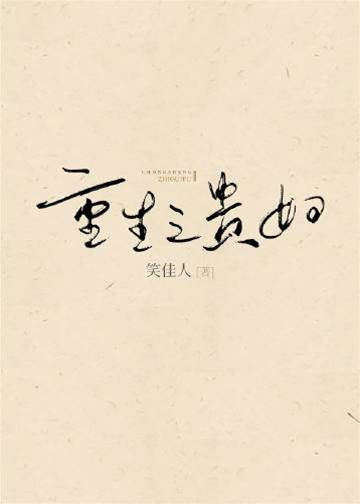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1 1876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