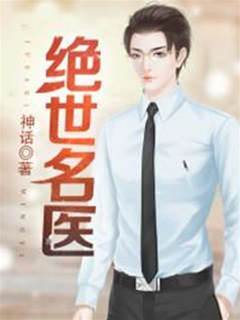《隔壁的小書生》 第98章 二更
那兩名衙役帶著孟三人回到剛才郎知府進的酒樓里, 客客氣氣請他們在一間屋子里坐下,外頭又給上了好茶好點心。
孟再一次問他們請自己過來做什麼,但那兩個衙役只是搖頭, 說是知府大人的命令, 的卻什麼都不知道。
眼見問不出來,孟也只好放棄。
廖雁倒不客氣, 先拿起來聞了下,覺得沒有毒, 直接抓著就吃, 一邊吃還一邊問:“我說書呆子, 我看他們就是沖你來的, 你別是在老家犯了什麼事兒,給人在這兒認出來了吧?”
孟失笑, “若果然如此,咱們這會兒就該在大牢里了,又怎麼能吃什麼點心喝什麼茶。”
說這話的時候, 他還往外頭瞧了眼,并沒發現樓下有人看守, 安心的同時也越加疑。
廖雁也不過是胡說一氣, 見孟自己也猜不到, 索就專心吃喝, 不再過問。
既來之則安之, 兵來將擋, 水來土掩, 大不了打殺出去,怕什麼?
這家酒樓本就是南京城數一數二的高檔酒店,尋常百姓本吃不起, 里面的點心糕餅自然有其獨到之。
白星吃了兩塊,就覺得好像真的跟外頭賣的不大一樣,但哪不一樣,卻又說不上來。
把盤子里的將近十樣點心吃了個遍,據喜好分出一二三來,然后又跟孟換意見……
大街上的舞龍舞獅已經告一段落,外面圍觀的百姓漸漸散去,只剩下有資格進酒樓的讀書人們,環境頓時安靜下來。
孟他們三個坐在屋子里就能聽見外面那位郎知府勉勵眾學子的聲音,一干書生們激涕零的回應聲等等。
廖雁著窗往外看,目所及之,全都是神肅穆中摻雜著激的儒生們,不由嗤笑出聲,“這下可真算是掉到書呆子窩里了。”
這輩子都沒見過這麼些書生,覺連空氣都帶了酸臭味,嘖嘖。
南方的天,小孩子的臉,剛還是萬里無云,這會兒卻又不知從哪飄來幾朵烏云,隨隨便便往太上一擋便悄無聲息下起雨來。
唉,真是無禮!
細細的雨像牛,像針尖,本濺不起漣漪,落在外面繁茂的樹木葉片上,發出蠶食桑葉一般的沙沙聲。
其實這種程度的雨最惱人。
你說打傘吧,好像有點不值當的;
可若是不打傘?走一段路也就被淋了……
本地百姓早已適應了這種天氣,遇事一點都不慌,干脆利落的就近找一店鋪、雨棚,隨便一躲。
沒準還能跟店中的掌柜和伙計嘮兩句呢。
說說家里的事,說說清明的安排,說說今年要養多蠶紡多……
那位郎知府又勉勵幾句,就出了幾個題目,讓在場書生都在規定時間做一首詞、一首詩,外加一篇文章,還說會親自點評,讓他們務必用心。
卻說下頭那些讀書人大多出普通,十年寒窗也不過為一朝揚名,眼見機會手可及,焉能不激?
若果然能得了知府大人青眼,或被舉薦,或得到師徒名分,日后可就要事半功倍,平步青云啦。
郎知府捻著胡須略轉了兩圈,似乎對治下學子們的才華十分滿意,頻頻頷首。
他后還跟著幾位員,以及先生打扮的老先生們,約麼是本地府學的教授……
眾人一邊走一邊討論轉了一圈,郎知府便讓各自行,自己則借口更,臨時退場。
“哎哎,過來了過來了!”廖雁低聲道。
孟和白星一聽,趕把里的點心殘渣咽下去,喝了茶漱口,又相互檢查對方的手腳,覺得沒有破綻,這才站起來準備迎接。
輸人不輸陣,不管對方是敵是友,總不好讓自己看上去太過狼狽。
“你們在外候著。”郎知府的聲音低沉而溫和,跟他的外表很相符,人一聽就不自覺聯想起那種沉穩可靠的長輩。
他把幾個隨從都安排在門外,自己親自推門進來,抬頭就見三個小的正滿臉警惕加疑的瞅著自己,像一窩驚的小兔子,心中突然有些好笑。
“坐吧,不必拘禮。”他朝兩邊擺了擺手,自己率先在上首坐了。
白星和廖雁都是直來直往的子,既然對方他們坐,當下不再遲疑,直接一屁坐下。
倒是孟猶豫了下,見對方沖自己微笑頷首,這才別別扭扭地坐下。
這位大人似乎對自己十分親近,莫非……
他暗中打量著對方,不知是不是錯覺?好像也覺得對方有點面善,心中約升起一個猜測。
“你孟?”孟還在猜想時,郎知府先就發問了。
像,真像,真是太像了。
孟一愣,點頭,“是。”
郎知府不易察覺的松了口氣,忽然沖他笑了笑,“還記得我嗎?”
孟微微睜大了眼睛,與他對視片刻后,記憶深藏的某個角落突然被翻,像塵封的泥土掀起陣陣塵埃,終于進一,照亮了幾張泛黃的舊畫紙。
“您是……郎文逸郎伯伯?!”他驚喜加道。
那邊白星和廖雁飛快地眨著眼睛,本能的對視一眼:
呦,這怎麼個意思?認親嗎?
這個什麼狼伯伯熊伯伯的,看面相應該不到五十歲,可頭發卻白了大半,一雙眼睛里也滿是滄桑,似乎又比尋常四十來歲的中年人更苦相一點。
郎文逸點點頭,眼神迅速變得而慈,“想起來了?”
他的眼神像春風像細雨,就像看自己的兒子一樣溫慈,將人包裹。
孟嗯了聲,有點不好意思的了手指,“當年我還太小,這麼多年過去,您……我也記不大清了。”
他已經許久沒被人這樣看過了,忽然有點不適應。
他腦海中關于對方的最后一點記憶好像還是自己六歲生日時,對方抱著自己說笑,好像還給自己掛了一個玉質的項圈。不過后來孟家被抄,什麼都沒了……
“是我老了吧?”郎文逸笑著搖了搖頭,又抬手臉上的皺紋,“十多年啦!”
十多年的時,足以讓長青年,讓青年歷盡滄桑。
是人非啊。
孟的思緒好像一下子就被拉回到十多年前,心中百集,又酸又。
這十多年的歲月就像一條長河,那翻滾在歲月間的記憶碎片,就像流的河水,他曾無數次在冰冷的河水中掙扎,無數次徘徊在被溺斃的邊緣……但現在一切都過去了。
他被別人拉上岸,終于可以冷靜地回首自己淌過的河流。
孟記事很早,他約記得好像當年郎伯伯就已經至知府,怎麼這麼多年過去?還在原地踏步,說不通呀……
莫非……是被當年自家的事牽連了嗎?
郎伯伯與自家父親曾都在一家書院讀書,并拜一位大儒為師,有多年師兄弟名分,很深厚。
后來朝廷,連同孟家在的幾個大家族一夜之間分崩離析,其余關系親的也多被遷怒,或貶,或削爵,多年經營毀于一旦。
“您……”孟才要說話,郎文逸卻先一步問道:“這些年你都去哪兒了?我跟你伯母一直在四尋找你的下落,奈何一直沒有消息……”
那麼點大的孩子,獨自在外可怎麼活呢?
這麼多年沒有消息,他們夫妻不止一次的懷疑:是不是那個孩子已經死了?
但每次這個念頭一冒出來,卻又被他們強行打散。活要見人,死要見尸,只要沒見到尸,總還有活著的希不是嗎?
回想起過去十多年的經歷,孟一時也是慨萬千。
不過他并不是喜歡抱怨和訴苦的人,既然事已經過去了,又何必再提。
“就到走,后來到了一個小鎮子,遇到了一些好心人……”
說走只是好聽的,最初兩年,他幾乎是四流浪居無定所,如果不是桃花鎮的人,或許他真的早就已經死了。
郎文逸自己也是從底下爬上來的,自然知道一個無依無靠的孩子想要存活是多麼不易,不由一陣心酸。
不過現在看孟神飽滿雙目有,也略略到一點安。
可短暫的安之后,卻又是鋪天蓋地的憾。
多麼可惜!
這孩子自小天資聰穎,若未曾遭遇變故,必有三鼎甲之才……
只是現在再說什麼也沒用,只能嘆一句造化弄人。
“聽你的口音,倒像是在北地住過不日子,”郎文逸揮去腦海中不切實際的念頭,關切道,“怎麼又到這里來了?”
孟笑著指了指白星和廖雁,“總在家里憋著怪悶的,跟兩個朋友出來玩,也長長見識。”
郎文逸早就注意到他邊這兩個年紀相仿的伙伴,雖沒開口問,但一眼過去就覺得江湖氣甚重,也讓他越發好奇和心疼起這個侄兒過去這麼多年的遭遇了:
若他還是孟家的寶,又怎會跟這些江湖客扯上瓜葛?
不過既然還有閑逸致出來玩,至能證明他這兩年的日子還能過得去吧?
“多謝你們對兒的照顧,”郎文逸就像一位普通的家長對孩子的朋友那樣說話,他看了看兩人手邊幾乎空了的盤子,非常和氣地問:“再要點點心嗎?”
既然是外出,恐怕還是這兩位江湖小朋友照顧自家侄兒的時候多些吧!
白星和廖雁對和氣的人沒有什麼抵抗力,但也從來不知道客氣,于是爽快點頭。
這里的點心真的很好吃呀。
甚至廖雁還特意點單:“那個黃的五個瓣的多來點!”
郎文逸直接就笑了。
他已經很多年沒見過這麼有趣的小朋友了。
簡單直白,赤子心,很不錯,這樣的人跟兒打起道來,彼此省心。
“既然來到這里就算到家了,”郎文逸緩緩吐出一口氣,對孟笑道,“你這兩個朋友也不要到去了,都去家里住著,回頭若再想去什麼地方玩,只管說與我聽。你伯母想得你苦,快看看你,也省得日夜牽腸掛肚。”
就在幾個時辰之前,他是萬萬不敢想有生之年,竟然能夠找到師兄的孤!
廖雁輕輕了白星的胳膊肘,小聲道:“這兒好像還疼書呆子的……”
孟年的遭遇他不知道,但聯系對方的言行舉止以及日常生活習慣也略微能猜出一點來,如今見這位知府大人的關懷沒有一摻假,倒不像個壞人。
他了下,“書呆該不會呆在這兒不走了吧?”
白星一愣,拼命搖頭:不可能!
他說好了要跟自己去看荷花的!
孟卻搖了搖頭,語氣雖然溫和卻也很堅定的說:“登門拜訪是應當的,只是……只是我們過不幾天就要去往別了,倒不必再往府上叨擾。”
白星暗自松了口氣。
郎文逸是何等聰慧人?瞬間明白了他的擔憂,“當年的事都已經過去了,你不必想太多,更不必擔心連累誰。”
這孩子打小就早慧,偏又經歷那麼多磨難,想必心思越發細膩了。
孟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下,一針見道:“可伯父,您還是被連累了不是嗎?”
郎文逸張了張,想說什麼都化作一聲長嘆,“你呀,小小年紀的人。不要想那麼多。”
若真要說他一點沒被波及,那是謊話。
先生都曾說過他是天生做的材料,如魚得水,左右逢源……這些詞都可以套在他上。
早在當年事發之前,他已至知府,乃是一干師兄弟之中階最高之人,可謂前途無量。
奈何世事無常,孟家一夜之間被連斬除,他冒死上折子求,非但沒能挽回,反而惹得龍震怒,被貶去西南偏遠之地做了縣令。
西南邊陲之地悶熱,又有毒蟲瘴氣,還時常有倭寇滋擾,被打發去那兒的員可謂九死一生。他一個土生土長的北方人,長途跋涉過到那里本不適應,全家老小一病半年,險些就死在那兒了。
可能他們家人天生命,竟生生扛了過來。他本人也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反而發圖強,短短五年之就讓那個破落小縣城大變樣。
他的政績實在太過突出,而且皇帝其實也頗為欣賞他危機時刻還不忘同門誼的人品和心,就順水推舟提拔他為知州。
也是通過這件事,郎文逸看到了希,于是接下來幾年幾乎是玩命一樣的干,終于又一步步爬回十年前屬于自己的位置……
此時再說這些,好像也不過三言兩語的事,但只有親經歷的人才知道這中間有多風險。
但凡稍有差池,就是萬劫不復。
郎文逸今年也才四十六歲,可頭發已經花白,更落下一病。
偶爾夜深人靜,因為各疼痛睡不著覺時,郎文逸也會對著月亮慨萬千……
“其實當年的事,陛下也是迫不得已,如今既然已經過去,他……”郎文逸的話還沒有說完,卻見從相認之后一直都溫和的侄兒忽然暴躁道:
“不要再提個人了!”
莫說郎文逸,就連白星和廖雁都被嚇了一跳。
后者手一抖,淡黃的五瓣杏花餅掉到地上,咕嚕嚕滾出去老遠,最后撞到桌角才不不愿地停下來。
相互認識這麼久了,他們從未見孟如此激,又如此失態。
他的眼圈迅速泛紅,抓著椅子的手關節都泛白了,額頭上也青筋暴起,顯然抑到極致。
“……”白星立刻握住他的手。
手背上的溫暖瞬間驅散了徹骨的寒意,孟好像從噩夢中驚醒一樣狠狠了一口氣,面慘白,勉強沖習慣扯了扯角,“我沒事。”
白星的眉頭皺得死。
怎麼會沒事呢?你的臉都白了呀。
“那個人?”郎文逸愣了會才回過神來,驚道:“你是說陛下!”
孟兩片用力抿著,牙關咬,雖然沒有做聲,但他上的每一頭發都出肯定的意味。
郎文逸簡直被驚呆了。
那可是九五至尊呀,怎麼能如此不敬?
若換作旁人,他必然要出聲斥責的,可面對這個孩子,他卻一句重話都說不出來。
郎文逸重重嘆了口氣,努力把聲音放的和,“你是在怨陛下嗎?其實當年的事他也很后悔,但是沒有辦法呀……”
這些年他也時常與留守京城的友人書信往來,聽說陛下曾無數次不經意間喚“孟卿”,偶爾還會見到他頗為落寞的神。顯然,當年的事并非像外界猜測那樣,沒有在他心中留下一憾。
“我為什麼不能怪他?”誰知孟非但沒有聽勸,反而越發激起來,抬高了聲音喊道。
猜你喜歡
-
完結11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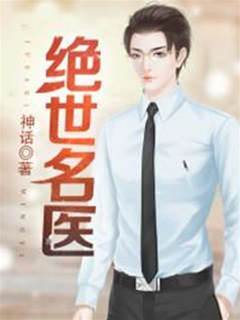
絕世名醫
為了保護姚玉蓮不被欺負,劉大柱挺身而出。他學醫術,練武功,救死扶傷,帶領村民勤勞致富,從一個落魄的毛頭小子變成遠近聞名的大人物。 村里的小媳婦大姑娘不淡定了,連城里的年輕女老板,還有女明星女老外都爭先恐后的要跟他交朋友。 “大柱,快到我的碗里來……” “不去,俺要回去給媳婦講故事……”
298.1萬字8 97487 -
完結839 章

大唐風華路
韓躍是個胸無大志的小人物,偶然穿越唐朝,有個童養媳,種著幾畝地,沒事發明點東西,他感覺這種日子挺好,如果沒有人打攪的話情愿一輩子都這樣。 然而男人總要長大,小混混也會慢慢變成大人物,舉手投足,會當凌絕頂,歲月是一把殺豬的刀,韓躍卻慢慢成了一把鋒利的劍。 大唐風華,誰人領舞,這是一個小混混慢慢成長為大人物的故事。 有裝逼,有犯渾,有發財,當然也會有妹子……
209.7萬字8 64568 -
連載11297 章

丑女種田:山里漢寵妻無度/錦繡農女種田忙
又胖又傻的丑女楊若晴在村子里備受嘲弄,被訂了娃娃親的男人逼迫跳河。再次醒來,身體里靈魂被頂級特工取代,面對一貧如洗的家境,她帶領全家,從一點一滴辛勤種田,漸漸的發家致富起來。在努力種田的同時,她治好暗傷,身材變好,成了大美人,山里的獵戶漢子在她從丑到美都不離不棄,寵溺無度,比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好多了,豈料獵戶漢子不單純,他的身份竟然不一般。
1988萬字8.46 776146 -
完結634 章

醫品廚娘食運當頭
穿成貧苦小農女,被賣給瞎眼庶民做妻,顧瑾妤擼起袖子決定:“創業!” 一雙巧手烹百味,逆天醫術治病人。變美,變富,讓夫君重見光明。誰知道,這也能成團寵真千金?皇帝看著親閨女激動不已:“孩子,這是你的不成器的大哥二哥三哥,他們解決不了的,你拼爹。” 顧瑾妤舒服極了,“欺負我,我大哥大理寺少卿抓你坐牢,打我,我二哥大將軍操練你?看不起我,財勢通天皇商三哥拿錢砸你!” 說好搭伙過日子誰也別喜歡誰的瞎眼將軍,畫風也逐漸脫軌: “江山為聘,我的女人我自己寵!”
98.9萬字5 144914 -
完結412 章

農女有空間:拐個將軍去逃荒
大慶末年,災難頻生!東邊兵禍,西邊旱情!民不聊生,十室九空! 唐果兒一朝穿越,就趕上了逃荒大軍,黃沙遍野,寸草不生!左手是麵黃肌瘦的弟弟,右邊是現撿的胡子拉碴的大個兒拖油瓶!又看看自己弱不禁風的小身板! 隻想仰天長嘯一聲! 好在自己空間在手,吃喝不愁,看她怎麼帶著幼弟在這荒年裏掙出一番天地來! 呆萌女主:噯?!那個大個兒呢?! 腹黑將軍:你在問我嗎?
74.3萬字8 112392 -
完結443 章

我在末世當包租婆
被偏心的爹媽惡毒姐姐趕出家門,蘇桃決定跟他們一刀兩斷,餓死凍死,在外面流浪一輩子也不回家。誰知機緣巧合下綁定了包租婆系統,直接贈送了她三千平的安全區。渣爹一家擠一間房茍延殘喘,蘇桃一個人住把自己的小家收拾的舒舒服服,建了一間又一間新房,生意…
79.5萬字8.18 243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